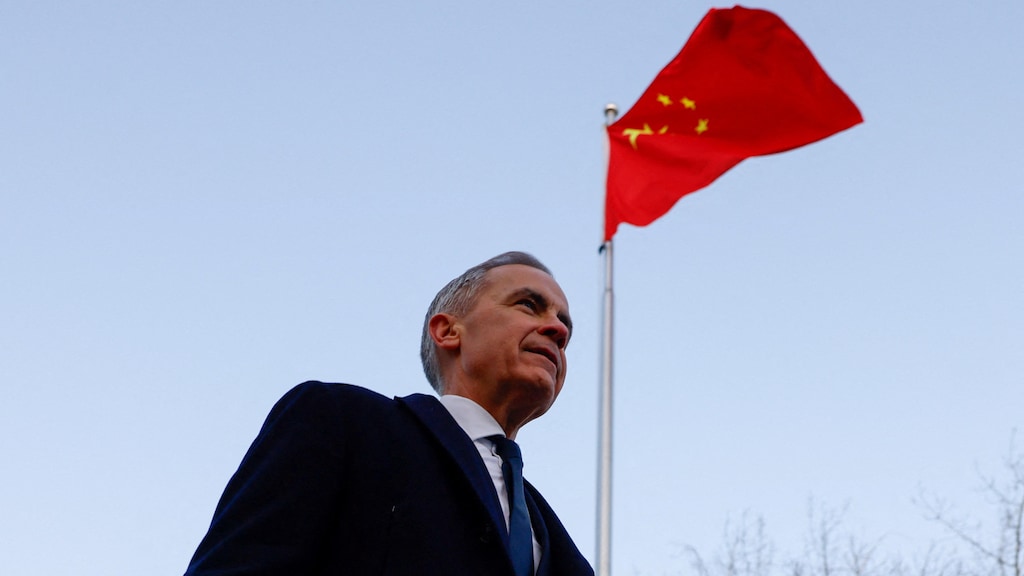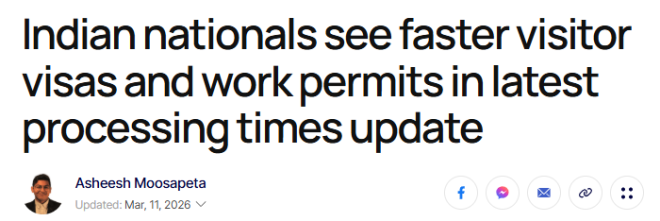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表了一篇 Jeff Gordinier 的文章。他是驻洛杉矶的一名记者,曾是美食评论家和作家,他的作品常聚焦于全球美食文化与餐饮趋势。其作品多次被《纽约时报》等媒体引用。
文章说,作家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1904 年出生于英格兰,近 40 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去世,但他的作品之所以经久不衰,部分原因在于其轻快的笔触。其作品《再见柏林》遵循了“轻松自然流派”(sprezzatura)风格,让读者感觉像山中溪谷里的一片树叶,另一部同类小说《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读起来亦轻松有趣。
事实上,当你阅读这两本书时,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有点像伊舍伍德笔下的人物,在德国柏林的一家夜总会里喝下四杯酒,以逃避现实。直到酒醒,发现现实还是那么糟糕。
伊舍伍德在《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第 90 页写道:“每周都有新的紧急法令。”当然,伊舍伍德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真实生活在柏林,当时纳粹在德国崛起,柏林陷入混乱和冲突。
在《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一书里,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诺里斯先生(Arthur Norris)身上,他是一位年事已高、戴着假发、患有牙科疾病的英国绅士,在柏林落魄从事间谍的勾当,以补贴自己对美酒和性怪癖的渴求。但是,在书中第 90 页和第 91 页的一大段直白段落中,作者写道:“间谍活动被发现了,但没有人真正关心。丑闻已经太多了。疲惫不堪的公众已经被猎奇的新闻折磨得消化不良。”
等等!你最近是不是很熟悉“疲惫不堪的公众 ”和 “猎奇的新闻”?自川普首次宣布竞选总统以来的十年间,美国选民被马拉松式的“推特治国”折磨得提不起精神。
小说接下来的段落带来了更大的痛苦。伊舍伍德写道:“柏林处于紧张状态。仇恨可能瞬间爆发,毫无征兆,不知从何而来;在街角、餐馆、电影院、舞厅、游泳池;在午夜、早上、中午;……在拥挤的街道中央,一个年轻人会突然遭到袭击,被剥光衣服、被殴打,血流如注地躺在人行道上;15 秒钟后,袭击者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帖子和言论:如果你碰巧生活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你会怎么做?伊舍伍德通过《再见柏林》准确地告诉了我们当时人们的行为方式。英国作家莱恩(Olivia Laing)说:“没有一本书能像这本书一样,展示政治和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或者说法西斯崛起在一个普通的、我们熟知的社会中是什么样子。”
许多德国人在紧急法令和公民规范遭到严重侵蚀的情况下所做的事情,与许多美国人现在所做的事情如出一辙:交房租、见朋友、做晚饭、听音乐会、度过每一天。两个地区似乎没什么不同,但德国人当时焦虑不安,不停地喝酒。
伊舍伍德在《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的结尾一章写道:“柏林一广场上,人们穿着大衣坐在咖啡馆门前,阅读着巴伐利亚啤酒馆政变(希特勒初登政治舞台)的消息。一家冰淇淋店照常开着。穿着制服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成员来来往往,一脸严肃,好像在办什么重要的差事。” 作者没有继续写的是希特勒登台之后的德国如同脱缰的野马奔驰在悬崖边上。
不难发现,魏玛时代的德国与过去十年的美国有相似之处。伊舍伍德记录了一个性别多变的时代,一个左翼和右翼之间不可避免的政治摩擦的时代,一个摇摆不定的零工经济不可能继续发展的时代。
《再见柏林》和《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有一份兼职,如家庭教师、表演者、调酒师、情报线人、闲置房间出租者或施虐女王,甚至有人有多份兼职。最终,他们所寻求的都是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性、酒、歌舞、海滩旅行和其他娱乐活动,哪怕只有几个小时,也能让他们的注意力从即将到来的社会崩溃中转移开。
2025 年的秋天,在右翼活动家柯克(Charlie Kirk)被枪击以及随后的自由言论被控制之后,我们不可能忽视整个美国都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让美国传统价值观成为一种渴望已久的奢侈品。
在柯克遭枪击两天后,川普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米勒(Stephen Miller)做客福克斯一档新闻谈话类节目时,详细阐述了政府打击国内对手的计划:“我们不会生活在恐惧中,但你们将生活在流放中,因为在总统川普的领导下,我们会利用执法部门找到你们,剥夺你们的财富,剥夺你们的权力,如果你们触犯了法律,还将剥夺你们的自由。”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恩诺斯(Ryan Enos)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说:“柯克遇害后总统做了什么?他对政治对手的攻击纯属专制行为,他将柯克遇害视为实现其从政以来一直宣扬的机遇:利用国家权力惩罚那些违抗他的人。”
“魏玛共和国国会大厦纵火案使希特勒有借口迅速消灭了阻碍他夺权的反对党,使他有权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通过法律,暗暗攫取了专制权力,其后果如今看来如此严重。”
“纵观历史,领导人利用危机时刻扩张权力的模式清晰可见,这通常以牺牲法律程序或公民权利为代价。站在现实回望过去,我们能看清那些时刻的本质,但在当时,却难以反抗。”
对川普及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忠实拥趸而言,政府停摆、前FBI局长科米(James Comey)被刑事起诉以及柯克遭暗杀等都是送上门来的、可以大做文章的素材。
至于作家伊舍伍德,他不是傻瓜。到1933年,他可以看出德国快要变天,希特勒带领的政党由于注入了种族主义保守血液,导致面目异化,向极右翼发展。伊舍伍德作为一个左派同性恋者,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柏林。
作家巴克内尔(Katherine Bucknell)在关于伊舍伍德的传记中描述,1933 年伊舍伍德在柏林经历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目睹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焚书。她在书中写道:“5 月 10 日,他目睹了为销毁他所写的那类左派小说而点燃的巨大篝火。这是一场将犹太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性恋者、和平主义者和外国人的著作从德国文化中清除出去的净化之火(purification)。4万名德国市民聚集在一起,在濛濛细雨中观看戈培尔将数千本书付之一炬;当晚,德国许多城镇同时举行了类似的焚书活动。”
戈培尔当时宣称焚书标志德意志民族思想的新生,成为纳粹党控制意识形态、镇压思想自由的重要标志事件。
没有比这更明确的警告信号了。伊舍伍德在焚书后几天就赶往希腊,但1933年春天的噩梦伴随了他数十年。传记作家巴克内尔说:“这一幕萦绕了伊舍伍德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