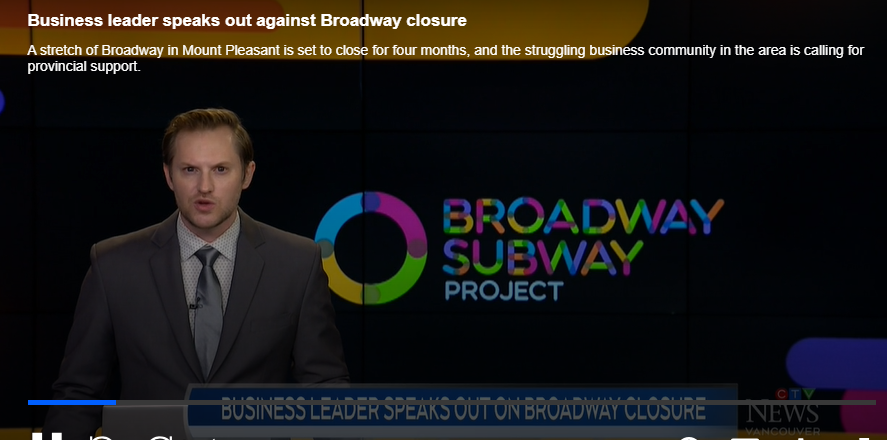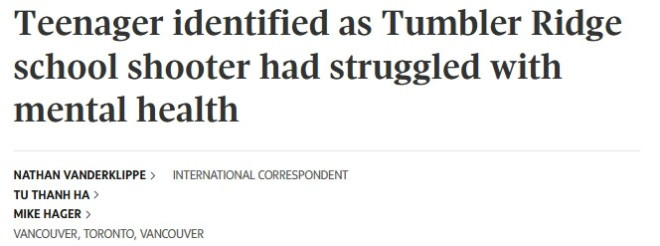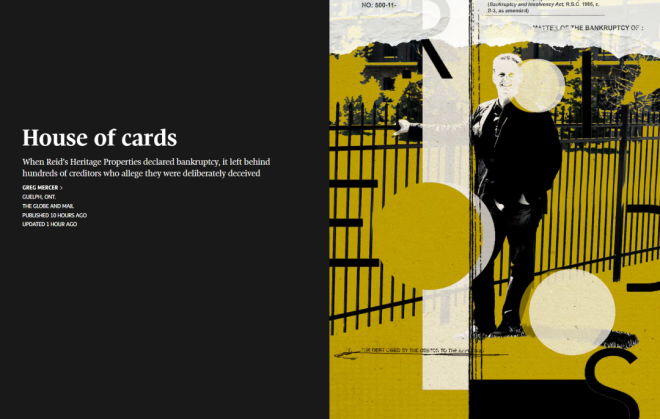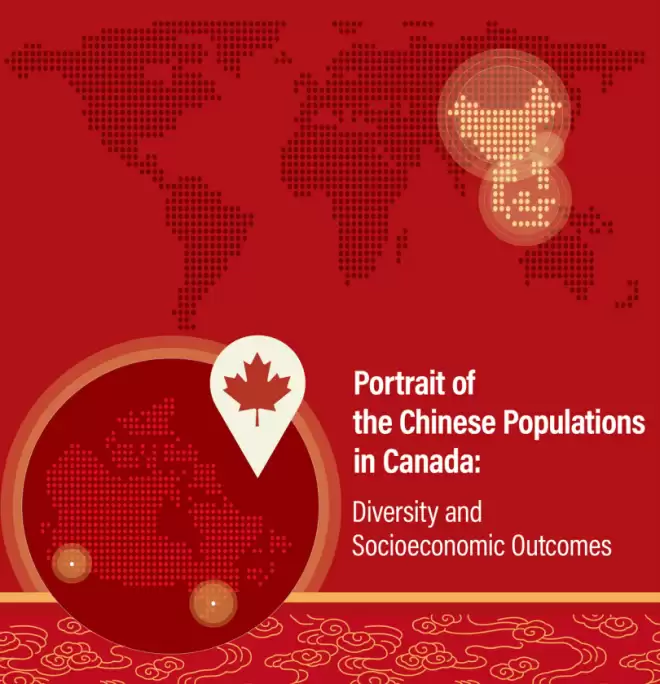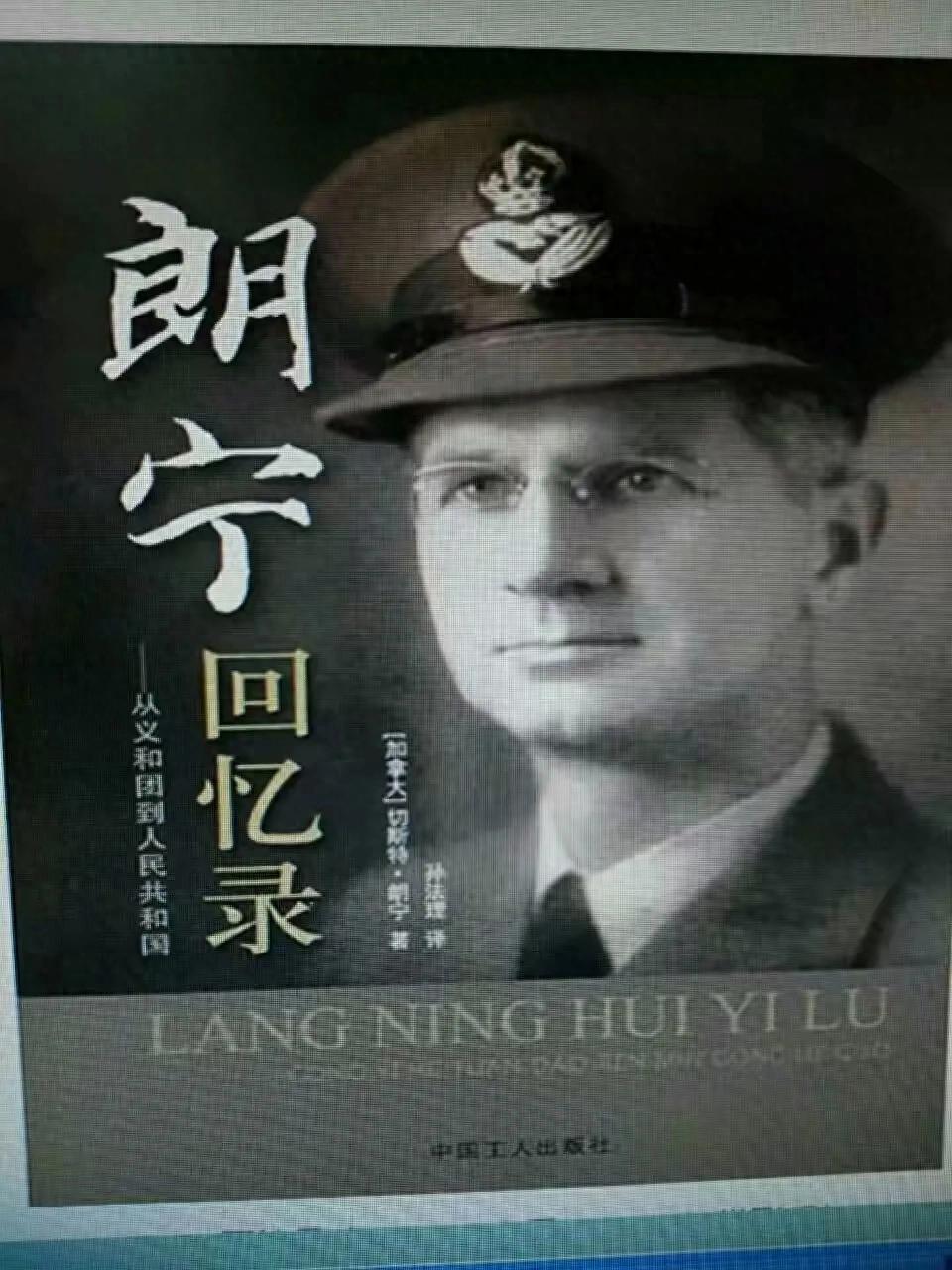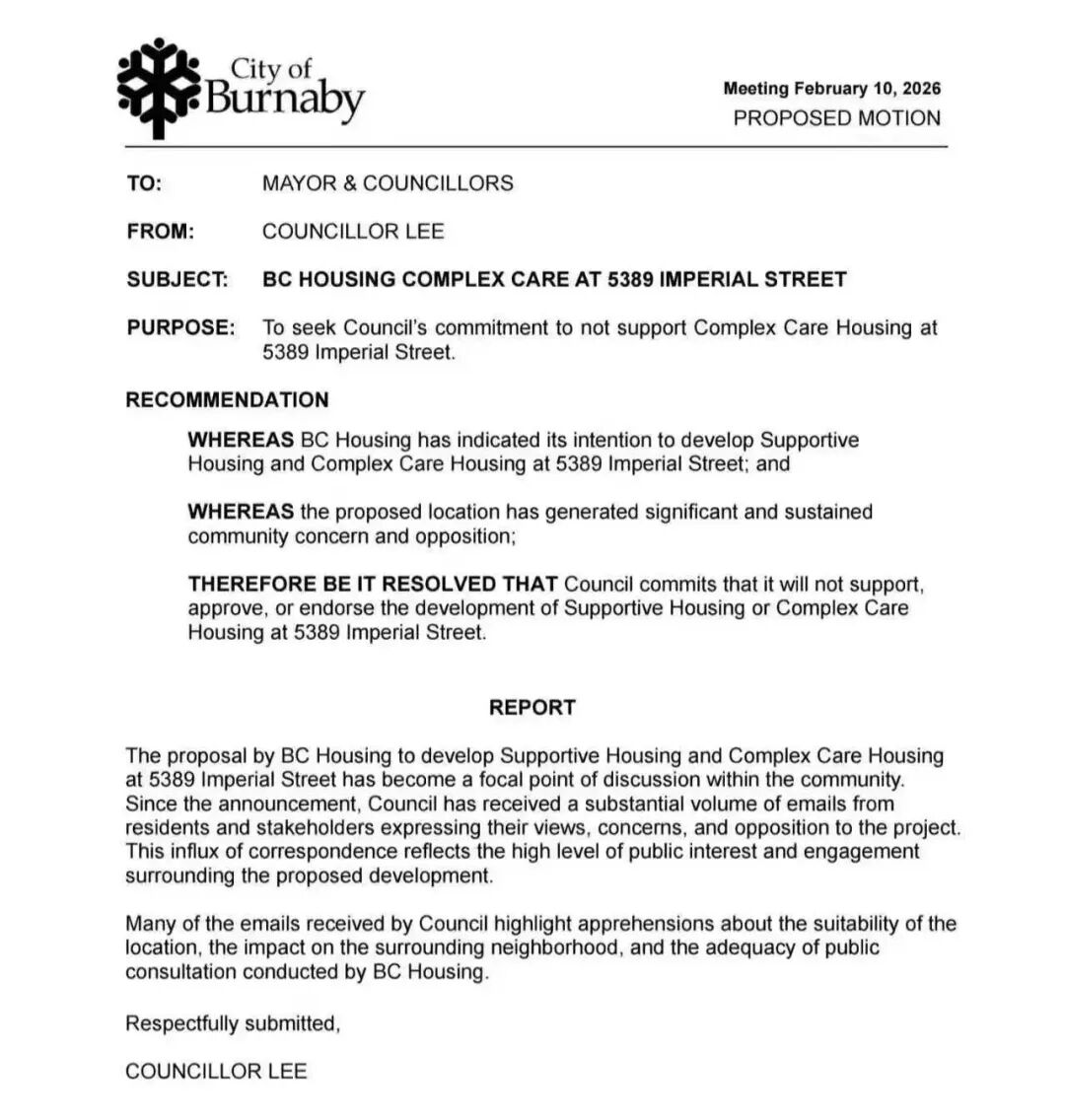刚来的时候,一切都不适应。空气是新的,街道是新的,连阳光照在身上的角度都不一样。语言听不懂,生活节奏也完全不同。去超市买个菜都手忙脚乱,看到满架子的英文标签,什么chicken breast、beef sirloin、celery,我一个都认不全。第一次去银行开户,柜台小姐问了几句,我一句也没听懂,只能尴尬地笑。她见我愣着,干脆拿出一张表格指给我看,那一刻我才体会到“听力不及格”的绝望。
那时候,朋友不多。放学回到小小的地下室,头顶传来楼上房东的脚步声,暖气机嗡嗡作响。房间里只有一张旧书桌、一张单人床,还有从国内带来的几包方便面。偶尔打电话回家,听到爸妈在电话那头的声音,鼻子就酸得不行。可国际长途太贵,一分钟都得掐着算,几句寒暄后就得赶紧挂断。那种孤独,是一种从语言到情感的彻底断层。
如果那时候有退路,或者说没有“沉没成本”,我可能真的就回国了。什么是沉没成本?就是那些已经花出去、回不来的成本。比如我第一年的学费——一万加币;还有为了出国而辞掉的那份体制内工作。那时候国内一个月工资才一千人民币,如果扭头回去,或许还能回单位上班,可是这张机票和那一年的学费就白白打水漂了。想想也就只能咬牙留下来。
留下来才发现,留学真是个“烧钱”的事儿。一年学费一万,两年专业课加半年语言课,光学费就要两万五。住宿、生活费另算。怎么办?只能“升级打怪”,边打工边读书。洗碗、送报、打杂,什么都干。不是不累,而是没得选。
刚来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寿司店当服务员。第一天上班,老板娘就叫我去冰箱里拿“avocado”。我傻傻地愣在那儿,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又补了一句“green one”,我才在一堆蔬菜里找到了一个奇怪的绿色果子。没想到,这个“鳄梨”竟成了我留学生活中最早记住的英文单词之一。干了两天,我被炒了。理由很简单——“too slow”。那天晚上,我抱着书包坐在公车上,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掠过玻璃,光影像一条流动的河。我盯着自己的倒影,心里一阵发酸,第一次有了“我是不是选错路”的念头。
那个时候我住在西区唐人街,在唐人街的川味轩打工,第一次看到下雪,好激动。但是渐渐的,我发现下雪可不好玩,冬天10点下班了,要自己走回家。关键是还没有雪靴,穿者餐馆的防滑鞋,到家时,鞋子都湿透了。

后来,我找到了一份超市收银的工作。那是一家华人开的店,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9点,一天12小时,中午和晚上各休息半小时,一周六天。周日还要去图书馆写作业。现在国内说的“996”,我算是提前体验过了。每天早上搭第一班地铁去上班,晚上一出门天都黑透了。冬天的时候,外面零下十几度,哈气结成白雾,地面滑得像镜子。
到下午6点的时候,脸上的肉都不自觉往下耷拉。客人问我:“你怎么不笑啊?”我心里苦笑——不是我不想笑,是真的笑不出来。那时候的我,只想着这一单结完,再下一单。因为收银员也有KPI,哪台机子结账多、哪台少,老板都会看。我们都在比谁的手更快,谁能少出错。晚上回家,脱下鞋,脚底一阵刺痛,整天站着,连脚趾都肿得发红。那种机械重复的日子,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没电的机器人。
但也正是那些日子,让我学会了咬牙和坚持。每一个不懂的英文单词、每一次被人误解的尴尬、每一分打工攒下的学费,最后都变成了我骨子里的韧劲。后来回头看,那段艰难的岁月像一块磨刀石,磨掉了青涩,也磨出了倔强。
05年夏天来的,09年移民就批下来了,好像是4月份登陆的。整个留学移民过程历时4年整。现在回想,那4年像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刚来时一身稚气,离开时已经能独立生活、独立思考。
这个移民速度够我吹一辈子的了。
弹指一挥间,我也来加拿大20年了。回望当年的自己,那个在地铁里拎着打工便当、英语磕磕巴巴的年轻人,我忽然很想拍拍她的肩膀说一句——“你做得很好,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