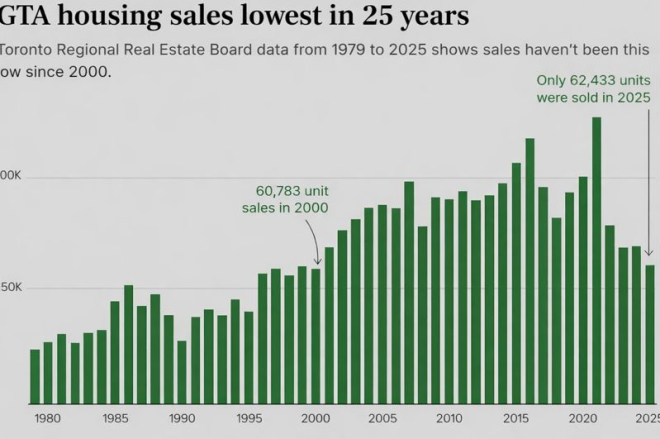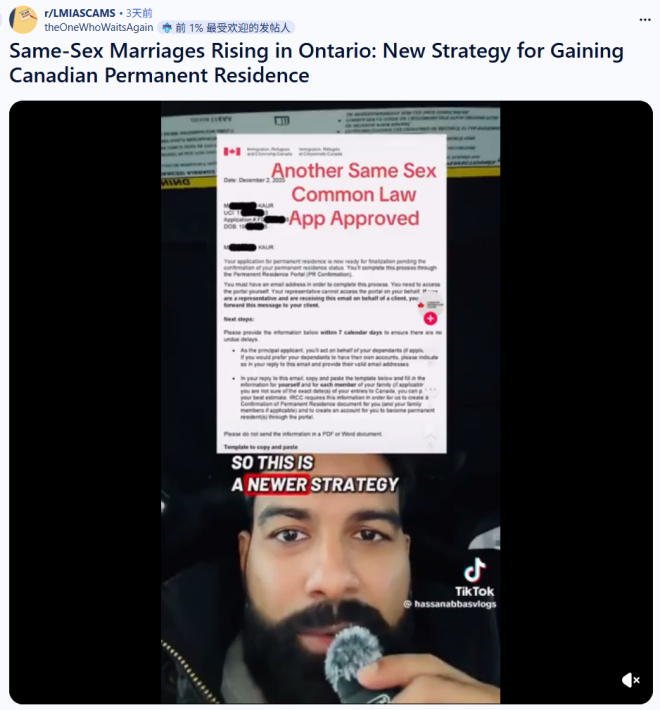在不少城市,垃圾分类已经介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但成效尚待评估。与此同时,一个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东部的偏远乡镇里,一场针对农村垃圾分类的实践已经持续了三年多,初步实现了垃圾处理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目标。
当垃圾分类这样一个看起来和“城市文明”高度相关的词,与一个曾经的贫困乡联系在一起时,问题随即产生:为什么一个在全国并不起眼的小乡镇,会成为农村垃圾分类的第一乡?在乡镇的地域空间里,垃圾分类的推行又面临着哪些困难?它的模式是否可持续、可复制?
早上7点,雾还未散尽,老管已经骑着他的垃圾收运车在村里转了一个小时。冬日的早晨,这座众山环抱的村庄里,植被上结了一层厚霜。老管穿一件迷彩大衣,戴胶质手套。在一个巷口,他停好车,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就提着一黄一绿两个小号垃圾桶出来了。黄色桶上印着“不会烂垃圾”,绿色桶上则是“会烂垃圾”。
和垃圾打了半辈子交道,直到成为管村的“垃圾收运员”后,老管才第一次得知,垃圾还可以这样分类。他今年63岁,妻子生病离世,儿子眼盲,是村里的低保户。此前他在村里干了多年的清洁工,眼里的垃圾只有两类:能卖钱的、不能卖钱的。
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工作都是把村里不能卖钱的垃圾清理出来,然后就地一把火烧掉,或者拉到村子后面的自留山上,找个坑倒进去了事。那个时候,管村的马路和田间地头,到处可见村民随手丢弃的烟盒、瓜子皮和塑料包装;公共垃圾桶周围永远堆满了垃圾,夏天臭味熏天,下大雨时,地上污水横流,垃圾冲得到处都是。平时靠人力清理不及,村民就把垃圾倾倒在河道边上,等着涨水时把它们冲走,因此河面上常年漂浮着各种塑料袋和烂旧衣服,还有从村民家化粪池里直接排出的粪便。一位当地的乡干部感叹:“老百姓基本就生活在垃圾堆里。”
事实上,管村的垃圾问题并不是个例,在更广阔的中国农村地区,还分布着无数个“管村”。它们有着相似的景象:塑料制品掺杂着其他生活垃圾,堆放在村子池塘、河道、路边等公共区域。这些地方堆满了,垃圾开始延伸到村民的院前屋后。时间久了,垃圾就像花草树木,成了一种广泛存在却又让人习以为常的角色——它们甚至可以挂在树枝上,也能渗入土壤。
据原环保总局和住建部的统计,到2007 年为止,农村地区的垃圾已致使1.3万公顷农田不能耕种,3 亿农民的水源被污染。至2016 年,中国农村地区垃圾年产生量已经达到了1.5 亿吨,相当于37万列高铁(8节车厢编组)的重量,其中只有一半经过了处理。
在这些未经处理的农村垃圾里,相当一部分是“不会烂垃圾”。在管村,它们称得上是“舶来品”,这些以塑料包装为主的白色垃圾,大多是来自工业社会的消费品。作为无机物,它们无法在土地中自然降解,打破了农村原有的生态循环体系。过去,村民种植稻谷和瓜果蔬菜作为食物,剩菜剩饭、烂菜叶和稻谷壳倒给猪鸭鹅作饲料,人畜产生的粪便再次回到地里,成为天然的肥料,供给农作物生长。
舶来的问题,需要用舶来的方案化解。如今,老管成了解决管村垃圾难题的重要一环。他和另一个垃圾收运员一起负责管村824户人家的垃圾,两人轮班,每两天收运一轮。
东阳乡垃圾收运员祝明山,他负责的龙溪村是当地第一个开展垃圾分类试点的村子(金海 摄)
老管开一辆专门为走街串巷准备的电动三轮车,车身宽度在120厘米左右,既能穿越狭长的小巷,也刚好放下两个并排的120升大号垃圾桶,一共放3排,6个。一个用来装“会烂垃圾”,其余5个用来装“不会烂垃圾”。在车身中间,两排垃圾桶的夹缝处,有一个长方形盒子,老管会将“不会烂垃圾”中的塑料瓶、酒瓶和纸板等可回收物,以及少量的废弃电池等“有害垃圾”拣出来,放在这里。
这种先由村民“干湿”二分,再由垃圾收运员二次分拣的做法是陈立雯带到管村所属的东阳乡的。她是个“80后”,在河北保定的农村长大,200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环保领域。此后6年的时间里,她调研了包括北京、武汉、江苏南通在内的多个地市,了解到如果处理失范,垃圾焚烧、填埋对人和环境的危害。2015年后,陈立雯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两所大学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2017年回国后,她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农村地区的垃圾分类。
陈立雯曾被不止一次问过,为什么要在农村地区开展垃圾分类。“我们在城市做过大量的垃圾分类调研,发现只能在某一层面解决问题,相比之下,农村地区更容易掉头,在这里,我们可以撬动整个系统。”陈立雯告诉本刊。
图源 | 《垃圾围村的海归挑战者》
现实考量之外,还有一直牵引着她的精神原点。在华北平原上长大的陈立雯,关于童年的快乐记忆,大部分来自房屋和农田间的半荒野地带,那里有坑塘、树林、麦场,和连成一片的菜园:夏天,小伙伴们一起听蝉鸣,一起在被雨水灌满的坑塘里游泳;秋天,是吃不完的酸甜枣子和金黄的烤玉米;冬天,早晨打开门,雪已经没过脚面,一路滑着雪上学去;一到春天,槐树开了花,成了最天然的零食。然而,这些带给她力量的荒野和土地,在离家后的20余年里,成为垃圾和污染问题的重灾区。陈立雯在后来的回忆文章里写道:“探索内心深处的原动力,是因为儿时生长的环境,潜移默化激发的,对人与环境共生的强烈需求。”
现在,陈立雯和她创办的“零废弃村落”公益组织,重点解决农村的垃圾分类问题。在他们探索出的这套已成体系的模式里,村民作为源头,“干湿”两分垃圾,垃圾收运企业上门收集后,将“不会烂垃圾”转运到城市里统一的填埋场或焚烧厂。“会烂垃圾”就地堆肥,变成“农家肥”,流入村民菜地,实现闭环循环——这是目前公认的解决农村厨余垃圾的最有效办法。
陈立雯告诉本刊记者,搭建这套垃圾分类体系,对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要求并不高。以堆肥为例,它的硬件要求简单,只需要一块平坦的硬化地面,再配上防雨棚、化粪池以及开放式围墙,满足自然通风、防雨、防渗的基本要求即可。此外,每家增加两个垃圾桶、每村增加一个垃圾收运员,算下来1.5万常住人口的东阳乡,人均只需要多投入5元钱。这套模式在东阳乡成功落地,成效显著。
然而,这种看似简单的模式,在陈立雯来到东阳乡之前的几次尝试中,都不同程度地失败了。
老管的垃圾收运车路线固定,一般从管村最北边的老房子开始。穿越促狭弯曲的石头小道后,就拐上了管村的主干道,一条干净平整的柏油路。早上7点半,路旁的猪肉摊、水果铺、自酿酒坊和卖炒粉的早餐店已经开张。主干道上没有公共垃圾桶,它们在实行垃圾分类后被撤掉了。在十字路口,两座小楼立在对角,分别是“东阳乡垃圾分类教育(展示)中心”和“垃圾再生馆”,招牌特意做成了绿底。
两座小楼由乡政府组织筹建,现在已经成为东阳乡对外展示垃圾分类成果的窗口。事实上,东阳乡垃圾分类工作,从一开始就是由乡政府主动推进的。在此之前,时任乡党委书记的王青海已经推行了五六年的垃圾治理工作。
2011年王青海到任时,东阳乡因为区位偏远,缺少工业基础,在整个广丰区(当时还是广丰县)的排名中,“长年绩效考核全区倒数”。“落后”的另一面,是东阳乡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因为地处低山丘陵区,东阳乡周围是延绵不绝的森林和山丘,两条河穿流而过。乡里的龙溪村在2016年时,还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保存完好的祠堂、戏台,还有马厩等黑瓦高墙的古建筑与江南山水融为一体,早晚时分柔和的阳光洒下,就像一幅水墨画。
东阳乡垃圾分类的推行,离不开前乡党委书记王青海的坚持(金海 摄)
大学读环境专业的王青海发现,东阳乡的出路就在眼前,而不是当时流行的搞工业、建园区,“搞农业和旅游业应该非常合适”。
定了发展方向,首先就要解决“脏乱差”的问题,东阳乡的垃圾治理工作在此背景下开始了。首先是清理陈年垃圾,清淤村现任党支部书记管宝良告诉本刊,仅这一项工作就持续了三四年。“房前屋后边边角角的垃圾,常年积攒,经过一层层的碾压,这次清干净了,一下雨,又冲出来好多,都是塑料破布、尿不湿、烂衣服之类的东西。河里也是,垃圾被一年又一年的沙子覆盖,发一次大水,冲出来一层,第二年,再冲出来一层。”管宝良说,有一年,他们清理出来的陈年垃圾装满了20多辆拖拉机。
实际上,作为一种“现代文明病”,很多管村人过去甚至不知道何为“垃圾”。管村村民周双爱今年52岁,1994年嫁到管村,在她的记忆里,当时管村还没有大的商业超市和固定的集市,家家户户种菜和水稻,小孩的零食就是自家做的米糕、蒸葛根、晒红薯干。平时盛东西用的是村民自己编的柳筐和竹篮。谁家杀猪了,去买肉,也是用稻草绑着拎回来,买豆腐用碗盛,买白糖用纸包。
2006年之后,周双爱明显感觉到村里垃圾开始变多。那时,管村已经开了几家超市,货架上永远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塑料包装,它们几乎是侵入式地进入农村生活,快速取代那些原始的竹篮、柳筐;同时出现的,还有价格低廉、取用便利的一次性水杯、保鲜膜等;以前,村民驱赶鸟类用的是稻草扎的小人,后来,小人变成了竹竿上挂一个颜色鲜艳的塑料袋。它们被弃用后,一部分进了村民的灶火间,更多地,堆积在了田间地头、坑塘水渠,成为无法消失的垃圾。
王青海到任后,村里建起了垃圾池、垃圾屋,也放了不少公共垃圾桶。周双爱记得,大概在2014年前后,村里还给每家每户发了小垃圾桶,希望大家改掉乱扔垃圾的毛病,但小垃圾桶装满后,还要拿到外面的公共垃圾桶里倒掉,不少人嫌麻烦。公共垃圾桶常常爆满,因为嫌弃,不少村民经常为了公共垃圾桶的摆放位置发生争执。
这种混合垃圾收集和处置的模式,的确缓解了管村的环境状况,但新的问题和更大的经济压力也随即产生。王青海说:“东阳乡离城区比较远,离填埋场60多公里,垃圾运输成本很高,当时县里(现为广丰区)的指导意见就是希望我们就地处理。”
这些堆积的垃圾,“烂不烂的全部放在一起”,清洁工一个人来不及收运时,晚上就就地烧掉。一位村民向本刊回忆,“塑料烧起来的味道真的很难闻,我有好几次实在忍不了,半夜提水去把火浇灭”。后来,乡里建了一些焖烧炉,但过了一两年,因为环保问题,上面要求垃圾不能烧。这些建起来不久的炉子就闲置了,如今那些尚未拆除的焚烧炉,仍然伫立在荒郊野地里。
在2017年,东阳乡引入了一家第三方清洁公司,成为整个广丰区第一个建立起统一的垃圾收运体系的乡镇。东阳乡的垃圾开始运往上饶市的垃圾填埋场,以59元一吨的价格统一处理。“到2018年,随时来检查环境卫生工作,整个广丰区23个乡镇里,我们都是第一名。”在“扫地”这件事上,王青海认为东阳乡已经做到了极致。但仅仅把垃圾扫走,“眼不见为净”,似乎还不够。当时有村民去过填埋场,“五分钟都待不了,回家中午饭都吃不下”。
王青海清楚垃圾处理提倡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我们只是把此地的垃圾搬到了彼地”。更何况,垃圾没有减量,拉去填埋、焚烧的成本高,乡里的财政压力也很大,再加上当时东阳乡管村是市政府挂点的扶贫村,乡里希望做一些创新举措。
多种因素交织下,管理者们决定再向前一步,探索更先进的垃圾处理模式。很快,他们就把目光集中到了垃圾分类。
决定做垃圾分类后,王青海上网搜索资料,发现全国农村地区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2018年,广丰区一位主管环境卫生的领导到河北培训,认识了陈立雯,然后把她介绍给了王青海。
2018年4月,王青海委托清洁公司老板钱凤梅等四人去拜访陈立雯时,她正在老家河北省保定市西蔡村搞垃圾分类实践。在此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她已经在五六个村庄进行过试点。她选择的第一个村庄是河北省涞水县的南峪村,一个位于太行山山脉脚下的村庄。
钱凤梅是东阳乡后阳村人,她的绿洁企业承担了东阳乡垃圾清运工作(金海 摄)
和中国大多数村庄的生态一样,2017年7月之前,南峪村没有专门的垃圾清运外包企业,垃圾的最终去向是20公里以外的一个山上。“在2017年、2018年时,中国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没有垃圾收运系统。”陈立雯说,直到2018年,国务院发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建立农村地区垃圾收运体系才被提上各地政府的议程。此后,农村环卫市场化才开始明显提速,垃圾随意填埋的现状有了一定扭转。陈立雯团队进入南峪村后,一家企业承包了包括南峪村在内的全县19个“美丽乡村”的垃圾收运工作。
一个月以后,村里90%以上的农户逐渐开始垃圾分类。南峪村每天可以分出50%左右的易腐烂垃圾,不可腐烂垃圾的压缩车从两天来村里一次,改成每周来一次,垃圾减量明显。
然而,最初在南峪村实行垃圾分类的那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宣传教育和督察工作都由“零废弃村落”承担,当地村委仅仅“口头支持”,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当时全村200多户垃圾分类所需的小垃圾桶、垃圾收运车、堆肥场建设等硬件购置费用,全部由陈立雯和当时所在的公益机构筹备。当地村委没有深入参与,也为后来南峪村垃圾分类的可持续性运转留下了隐患。
通常,陈立雯团队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村子建立一种模式、体系,这个体系的持续运转需要依靠当地的管理者和居民。三个月后,模式建立,陈立雯团队离开的时间也到了。可2018年4月,她第三次回访南峪村时,“堆肥场管理已经形同虚设。从堆肥场里的厨余垃圾里混合了大量塑料来看,源头分类情况也不太好”。
在南峪村遇到的可持续性问题,在后来的多个村庄实践中也反复出现。再后来,她和团队转战浙江金华、深圳等地的项目也都不了了之。
有了不成功的探索,陈立雯已经看到了以村级为单位推行垃圾分类时,可能会面临的管理问题——依靠村干部的意志有太多不确定性,农村垃圾分类持续做下去需要更“顶层”的设计。2018年东阳乡政府找到她时,陈立雯也正在寻找合适的乡镇单位。钱凤梅还记得第一次到陈立雯家的场景,在那个略显破旧的院子门口,陈立雯的父亲听说他们是来学垃圾分类的,当场就劝阻他们回去,“她读了那么多书,却和垃圾打交道”。老人掩饰不住的无奈,反而让钱凤梅有了信心,这个专家或许“靠谱”。
事实上,在跟陈立雯联系之前,王青海已经带着团队去别处调研过几次。东阳乡和浙江接壤,从村里出发,几分钟就能到浙江省境内。考察一圈下来,王青海发现当地的模式,要么造价高,要么要求工艺复杂,都不适合在东阳这样一个普通的中部地区乡镇推广。
接到钱凤梅一行从河北传来的消息后,王青海给陈立雯打了个电话,他担心的难题被一一解答:平均每个村只要投入一万多块钱,同时送到焚烧厂的垃圾量会减少一半,一加一减,摊算到全乡,人均每年增加的费用只有5块钱左右。此外,村民只做干湿两分。厨余垃圾就地堆肥,且保证不会出现发臭、生蛆等次生问题。
乡里要搞垃圾分类的消息传开后,一些村干部却对这项工作避之不及。清淤村是东阳乡最小的村子,只有265户人家,也是整个乡里最穷的村。村支书管宝良告诉本刊记者,一开始他也不愿意。“我们都怕死了,千万不要到我们村里来。”在陈立雯拍摄的纪录片《垃圾分类在东阳》里,他对着镜头回忆当时的想法:“(垃圾分类)好多城市都搞不好,我们哪能搞好?”
但乡里告诉各村支书,谁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将在修排水沟、污水处理管道等基础建设方面得到政策倾斜。被“挠到了痒处”的管宝良很快毛遂自荐,带领清淤村成为第二个开展垃圾分类的村子。村委上阵督导,白天跟车检查,记录下分错垃圾的家庭。晚上,就派和这些家庭关系好的村委委员“上门谈心”。
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子是龙溪村。周季花是当时的龙溪村党支书,她个子一米六左右,身材微胖。1月5日和本刊记者见面时,她穿一件黑色绒大衣,戴珍珠项链,脚上是一双粗跟皮鞋,走起路来噔噔响。2020年,57岁的周季花卸任村支书,过起了退休生活,平时担任村里腰鼓队和广场舞队的队长,带领着一帮老姐妹搞娱乐活动。
1999年,周季花就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她有自己的方法——处理垃圾这种生活上的事,还是得依靠妇女。东阳乡宗族观念重,她把女人们请到村里的祠堂吃饭,来不了的,就由家里的老人或者男人代替参加。那天,整个祝氏祠堂里摆了45桌酒席,拉上横幅,像过年一样热闹。周季花、陈立雯和钱凤梅站在祠堂高处的戏台上,各拿着一个垃圾桶给大家讲解,下面坐着村民和领导。陈立雯是外地人,讲话大家听不懂,钱凤梅更不知道说啥。“三个女人一台戏,那我必须把这个戏唱响。”周季花灵光一现,“不知道怎么分,那我们就先把猪能吃的放绿桶里,猪不能吃的放黄桶里。”后来,这句话在上海实行垃圾分类时再次被提起,火遍了全网。
开完动员大会第二天,垃圾分类就正式开始了。在此之前,乡里已经把分类用到的小垃圾桶发到村民家里,垃圾桶上写着每户人家的名字。同时,撤掉了村里的大垃圾桶、封上了垃圾池。龙溪村村委雇了两个监察员,连续一周时间,每天早上6点绿洁公司的垃圾收运员上门,陈立雯和监察员跟车入户,一点点告诉村民,“头发属于不会烂垃圾”“鸡蛋壳属于会烂垃圾”“贝壳属于会烂垃圾”“餐巾纸属于不会烂垃圾”……一周以后,除了个别的“顽固分子”,大部分人都学会了。
有人说,龙溪村的垃圾分类工作能推行得如此顺利,和这里的基础好有关。陈立雯否定了这种说法。一个对比是,2018年陈立雯在自己的老家西蔡村开展垃圾分类实验,村民参与度和龙溪村是差不多的。但因为缺乏机制保障,最终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
到2019年5月,垃圾分类就开始在东阳乡的12个村子全面推开。源头垃圾分类的准确率达到90%以上。垃圾减量效果也开始显现,“会烂垃圾”分类后就地堆肥处理,垃圾减量达到50%以上,全乡日均减量超5吨。
实行垃圾分类以后,老管转到了垃圾收运员的岗位。每月工资从600元涨到了2700元。现在的东阳乡,像老管这样的垃圾收运员一共17位,分散在12个村庄。
在村里转了两个小时后,老管的6个大垃圾桶装满了。垃圾中转站设在村外的马路边上,是一间60平方米左右的白色小屋,接收管村和邻近清淤村的垃圾。整个东阳乡一共有六七个这样的垃圾中转站,老管把“不会烂垃圾”运到这里,再由清洁公司的大车来收,运到100多公里外的铅山焚烧厂集中处理。大车一趟可以装5吨,刚好是东阳乡12个村子一天的垃圾产生量。
卸完垃圾,老管又拉着几个空桶返回管村,再收一趟。他每天跑半个村子,需要分两趟收完。收工前,他把“会烂垃圾”送到堆肥场。东阳乡现在也是两村共用一个堆肥场,一共六七个,大多分布在村子的外围。在自然腐化的过程中,老管只需要每7天左右翻一次堆。根据东阳乡政府的介绍,可腐垃圾初步堆肥成功,年合成有机肥达到200吨。这些有机肥最终由附近的村民自取,流入各家的菜地里。
冬天里,老管早上6点就开始走街串户收垃圾了(金海 摄)
看起来一切都进入了一个可持续的循环中。但和陈立雯的预期一致,东阳乡的垃圾分类推行一个月以后,开始出现反弹迹象。为了避免在其他村庄试点时那样虎头蛇尾,她和东阳乡政府在2019年6月就开始合作探索一种长效的监管与考核机制。三年下来,推出了各项政策,包括在村民之间评比出红黑榜家庭;在村庄之间以明察暗访的方式进行月、季度和年度的考核。年度考核前三名的村庄,能得到最高8000元的奖励等。
多年的农村垃圾分类实践让陈立雯早就意识到,一套执行力强的监管、考核机制对这项工作的可持续性开展有多重要。但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垃圾分类最持久的动力都是人们的“自觉”。
在城市,市民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界限分明,垃圾分类大多发生在自家屋子外的公共空间。如果对城市缺少归属感,“自觉”更多依靠的是每个人的公共意识,只能缓慢提升;在农村,除了自家门前的一亩三分地,无论是老树成荫的村口、长满野花的河边,还是平整的谷场,都常被称作“家乡”的一部分。在这里,“自觉”更多是埋在村民内心深处的乡土情怀,它们不需要被建立,只需要被唤醒。
如今,在东阳乡龙溪村走上一圈,会发现这里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种着蔬菜和果树,有成片的油菜、正在卷心的包菜,芥菜绿得发亮,还有黄澄澄的柚子挂在枝头,等待采摘。一位龙溪村村民告诉本刊,今年种的500棵红薯“一个有两斤”。说话时,他语气上扬,带着自豪的神情——这个正在快速现代化的村庄,很多东西都在改变,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仍然与土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感情——他把自己家的菜地只上有机肥当作一种成就。
周双爱早年在杭州、深圳打工,家里的田地几近荒废。几年前,考虑到“年纪大了,不想再出去”,回到管村定居。2020年她把荒废的菜地重新收拾了出来。夏天时,辣椒一根茎上结出二三十根小辣椒,黄瓜比胳膊还粗,秋天种红薯,冬天种白菜、萝卜,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她喜欢这种生活,虽然平淡,但让她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