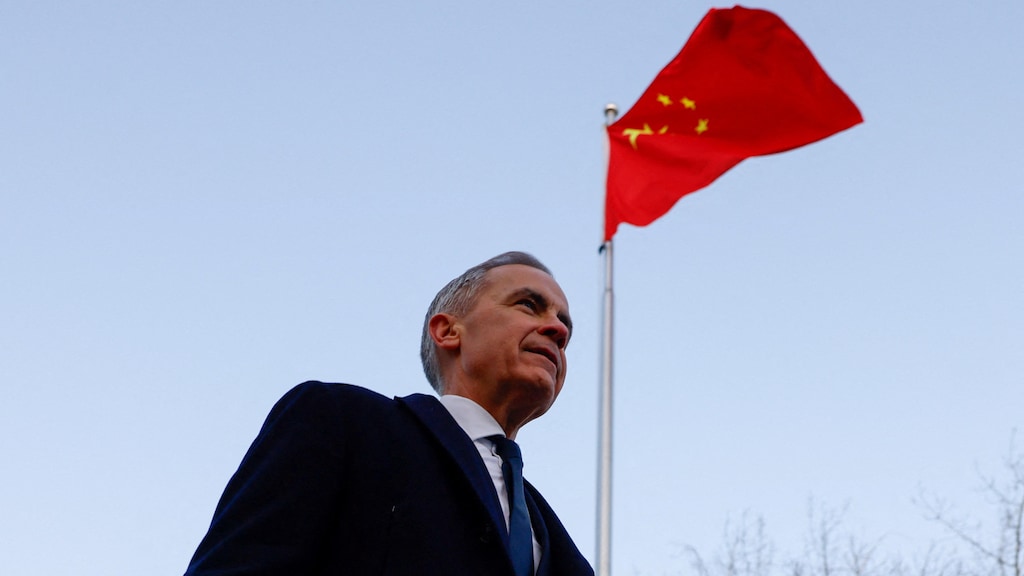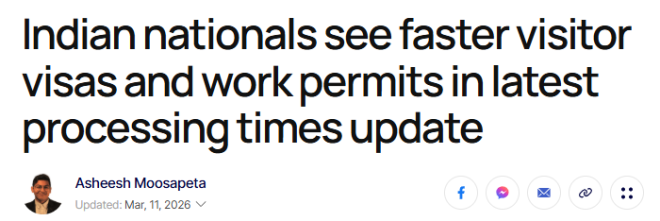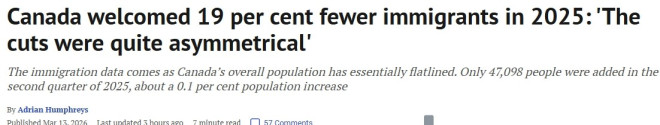毕生以新闻为职志的三民主义信徒徐新汉因癌症在加拿大过世,享年83岁,实践了他《中央日报》前辈陆铿的话:一日记者,终身记者。

参与创办温哥华《世界日报》编辑部的老友、前总编辑徐新汉因为癌症过世了。对我而言,这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去世前五天,我再次去列治文救世军的临终关怀中心探视他,他瘦得厉害,但意识记忆都十分清楚。我们畅谈因著《世界日报》的因缘际会,他精神十分不错。《世界日报》的前记者张宜中一直参与照料,我心中十分感动,这是超越了过往老总与部下的关系,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忘年交往的友谊,美丽且充满人性的光辉,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新汉兄与编辑部同仁的关系,远远不是雇佣或者工作关系可以定义的。
由于新汉兄表达强烈的为做事而生存的愿望,我鼓励他不妨跟治疗单位要求取得任何针对性新药的情况,争取“柳暗花明”的奇迹。我知道徐是三民主义信徒,就用国民党总裁孙文耳熟能详的金句激励他与癌症纠缠的斗志,那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刚巧,徐的女儿也到了,我又对她重复了一遍。这些对话,张宜中都按照徐新汉的愿望作了录影。张说,“徐总最高兴你来聊天”。其实,并非是我有什么激励人心的能力,而是新汉兄一生都是一个典型的“报人”,可谓为报纸而生、为报纸而鞠躬尽瘁。聊起他为之奋斗和贡献过的报纸,他有说不完的话,有无尽的回忆。
我跟他开玩笑,我一生唯一主动递过的求职履历,正是给他的,却杳无音信。那时候,我刚从东京来温哥华定居,与《世界日报》邂逅,很喜欢这份报纸,想去那里工作,就递了履历表,但却没有回音。我认识徐新汉之后,提起这件事,他常常认真解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日报》很难雇用大陆来的记者。不过,尽管没有在温哥华《世界日报》工作,但我在一九九七年应邀进入台北《世界日报》主笔阵,成为主要社论撰写者,一写就是十七年。由于台北总主笔的信任,我在选题上就有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因而将加拿大的重要事件开创性地在社论中一一表达出来。而在以往,加拿大议题从来不可能成为《世界日报》的社论选题。事后,徐告诉我,他很早就向台北总部要求,加拿大不应该受到美国“歧视”,报纸要追求全球视野,就不能无视加拿大。当加拿大议题的社论出现时,他十分高兴。我常常感到欣慰,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意中完成了新汉兄的心愿。
也因为撰写“世报”社论,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徐的同仁,彼此有了更多的交集。新世纪初,我在休士顿演讲时碰到新闻界前辈、“世报”终身副董事长、在我们接掌社论前负责每日社论撰写的马克任夫妇,他对社论的方向变化十分认同,也高度赞扬。会议结束后,他们夫妇邀请我去圣安东尼小游,途中谈及各地“世报”编辑部,他对徐新汉这个政治大学毕业的印尼华侨主持的温哥华编辑部颇多赞词。要知道,美国各地“世报”编辑部和多伦多编辑部老总当时大都是台北《联合报》系直派的,只有温哥华编辑部是新汉兄从头开始自己打拼出来、并受到台北高度认同的,而他自己是台北《中央日报》记者出身,并非联合报系的“嫡系”,这在当时是相当不易的。徐对办报的认真表现在一件小事上,他可以为一个标题和一句话表达得是否恰当,跟我讨论大半天。
但是,徐离开“世报”,并不是很开心的,他跟前社长的矛盾,也是编辑部同仁都清楚的,而大部分人是站在徐一边的,我也为他在台北说了话。但是,不高兴归不高兴,徐离开后,对《世界日报》依然关心,也积极收集他曾经任职的《新民国报》、国民党温哥华党部等各方面的侨社史料,建立网站披露这些史料,给研究者使用。此外,他也积极帮助大陆来的报业人士办报,实践了他《中央日报》前辈陆铿常说的一句话:一日记者,终身记者。
除了华文报刊,徐新汉也对加华文学十分上心,组织了作家协会,跟女儿两人为此奔走,组织活动、服务作家、参访各地,并邀请我当顾问,使我们在更多方面有交集。每次跟新汉兄交往,都能体会到他对中华文化的拳拳之心、对台湾和国民党前景的忧心忡忡。他作为东南亚侨生,对华侨社会始终关心,对中华文化的海外薪传更是身体力行,他生前担任的侨社职务无数,包括加西政大校友会会长、侨务顾问、加拿大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等,都做得开心专注,也拿得起、放得下,展现豁达心胸。
显然,我在他病榻之前的激励没能实现,他在周五(八月五日)卸下新闻人的劳苦重担,终于可以安息,享年八十三岁。我十分同意好友、前《世界日报》温哥华总编辑、分社社长韩尚平的评价:温哥华新闻界失去一位终身以新闻为职志的前辈楷模。
亚洲周刊2022/8/15-8/21 2022年33期 丁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