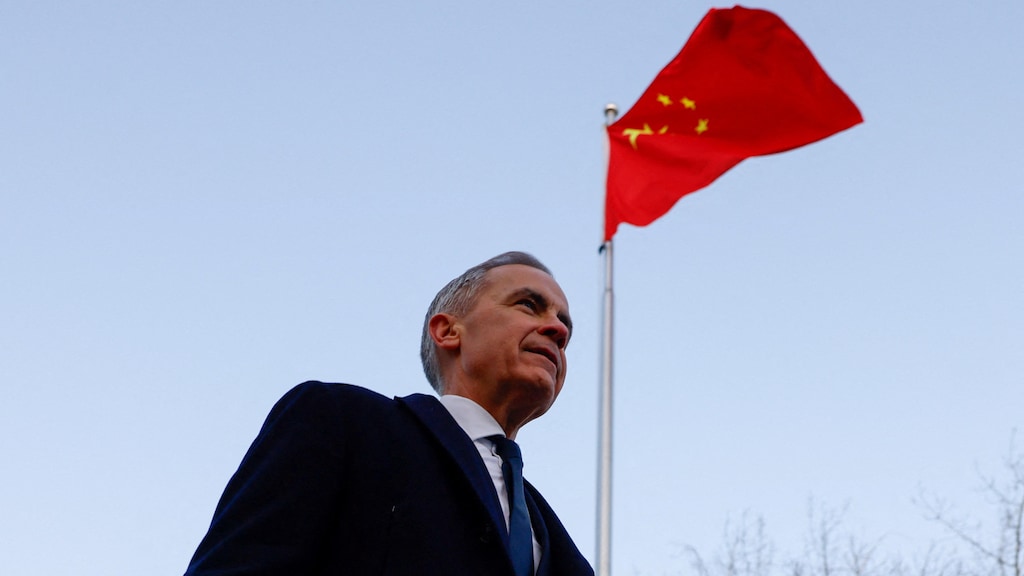在公共讨论中,很多人对某些政策感到不满,却常常把批评对象直接指向某一个政党。然而,这种做法往往并不能真正推动问题的解决。

无论是在联邦、省级还是市级层面,加拿大的法律和公共政策都不是由某一政党单方面决定的,而是由议会、政府部门、专家咨询和行政体系共同形成的结果。即便某一政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政策本身依然是制度运行的产物,而不是简单的“某党意志”。
因此,更有效的公共表达,应当聚焦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是否有效、是否产生了预期之外的后果,而不是把问题简化为“支持或反对某一个党”。
这一点,在加拿大持续多年的毒品危机中尤为明显。
反毒为什么必须非党派:因为它首先是“公共安全与生命议题”,而不是“阵营议题”
反毒(更准确说:反对毒品危机带来的死亡、犯罪、失序与青少年风险,反对不平衡的四支柱毒品政策的实践)之所以必须坚持非党派,并不是为了“中立好看”,而是因为党派化会直接削弱行动的有效性。
第一,毒品危机影响的是所有社区、所有家庭、所有阶层,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的“基本盘”。一旦反毒被贴上党派标签,支持者会被迫“选边站”,原本可以团结的家长、医护、社区组织、学校、商家与执法机构就会被分裂,公共议题变成互相审判动机的战场。
第二,反毒的目标是让政策改进并持续执行,而不是让某个党“输赢一局”。政党轮替是常态,如果反毒被绑定在某个党或某个政治人物身上,政策就会随着选举周期摇摆:今天推、明天撤;今天扩、明天缩。公共危机需要的是稳定的制度安排与跨周期的执行力,而非一次性情绪动员。换句话说,反毒的目标跟政党的目标有利益冲突。反毒的目标是毒品危机得到解决,党派的目标是为了“短期”执政,需要考虑多个议题。
第三,非党派更能让焦点回到“证据与结果”。反毒的核心问题是:哪些措施能减少死亡?哪些措施会造成外溢伤害(治安、公共空间、青少年暴露)?哪些资源配置最有效(戒治、精神健康、住房、执法、预防教育)?当讨论围绕数据、现实案例和执行效果展开,政府更难用“你在搞政治”来回避,也更容易形成跨党派的政策共识。
毒品政策:理念可以讨论,但结果必须检验
近年来,加拿大在毒品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以“公共卫生”为导向的政策尝试。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卑诗省针对小量非法毒品持有的去刑事化试点。这项政策的初衷,是减少对吸毒者的污名化,把成瘾问题从刑事司法系统中转移出来,鼓励人们寻求医疗和社会支持。
从理念上看,这种做法并非毫无道理。然而,政策实施后的现实情况却十分复杂。尽管去刑事化已经落地,卑诗省的药物过量死亡人数并未出现明显下降,反而在部分年份持续处于高位。大量公共讨论开始聚焦一个现实问题:如果死亡人数并没有减少,那么这项政策是否真正达到了其公共卫生目标?
这种质疑,本质上是对政策效果的评估,而不是对某个政党的攻击。但在实际舆论场中,这类讨论却很容易被引导为“你是在支持谁”、“你是不是反对某党”、“你站在哪个政治阵营”。一旦讨论滑向党派立场,政策本身的问题反而被掩盖,公众也失去了理性分析的空间。更糟糕的是,任何关于社区秩序、青少年风险、公共空间安全的担忧,都可能被简化成“政治口号”,从而错失修正政策的窗口期。
多方诉求并存,越需要用“非党派”把讨论拉回同一张桌子
事实上,毒品政策本身就涉及多个层面的博弈。公共卫生部门关注的是减少死亡和疾病,执法机构关注的是公共安全,社区居民关心的是生活环境和秩序,而医疗系统还要面对资源是否足够的问题。这些矛盾并不能用简单的“支持或反对某党”来解释,更不可能靠情绪化的政治对立来解决。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某党好或坏”的层面,就很难讨论更关键的问题:去刑事化是否必须与更大规模的戒毒治疗资源同步?现有的康复和精神健康服务是否足以承接新增需求?政策是否需要更明确的边界,以避免对社区和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
这些,才是真正值得公共讨论的问题。
而要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推动改进落地,就需要尽可能建立跨党派、跨立场的“公共联盟”:家长、学校、社区组织、医护、社工、警方、企业与各级政府部门,都能在同一框架下对话。
反毒的非党派立场,本质上是为“最大公约数”创造条件:不要求你先认同我投票给谁,但要求我们都认同生命必须被拯救、社区必须被保护、政策必须对结果负责。
聚焦政策本身,公民发声才更有力量
从公民参与的角度看,聚焦政策本身的批评和讨论,反而更有力量。当公众用事实、数据和现实案例来质疑一项政策的成效时,政府和议会更难回避这些声音,也更有可能在制度层面进行调整。
而如果讨论变成党派互骂,政策本身反而会被当作政治筹码,而不是需要修正的公共事务。有些人会认为,只要自己“清白”、“不碰毒品”,政策变化与自己无关。但现实是,法律一旦通过,影响的并不仅是少数群体,而是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等到政策执行过程中对个人、家庭或社区产生直接影响时,再试图通过抗议或维权去扭转,往往需要付出极其漫长的时间成本。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法律和政策的制定阶段,才是公众参与最关键的窗口期。更重要的是,加拿大许多标志性的公共政策,往往不是某一个党“独自完成”的,而是跨党派、跨周期的制度接力:一个政府提出方向,另一个政府将其写入法律,再由不同党派在不同阶段补强细则与执行。这也是为什么公共议题(尤其是反毒、公共安全、医疗、教育这类关乎生命与社区秩序的议题)更适合用非党派方式推进:你要推动的是“制度改进”,而不是“党派输赢”。
以多元文化政策为例:1971年10月8日,联邦自由党政府(总理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在众议院正式宣布多元文化为国家政策方向;随后在1988年7月21日,联邦进步保守党政府(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推动《加拿大多元文化法》获得御准并成为联邦法律,把“政策宣示”进一步升级为“法律制度化”。这条路径本身就说明:公共政策的成型,离不开议会讨论、委员会推动与跨党派共识,而不是某一个党单方面“拍板”。
再看加拿大引以为傲的全民医保,更是典型的“多党派共同塑形”。在省级层面,萨斯喀彻温省的CCF政府(合作联邦党,NDP前身)在省长汤米•道格拉斯领导下,率先在1947年推出普惠的公共住院保险,并在随后推动更完整的医疗保险制度;在联邦层面,1957 年,联邦自由党(总理路易•圣洛朗)政府提出并推动通过《Hospital Insurance and Diagnostic Services Act》,确立联邦—省住院与诊断服务的成本分摊框架;该框架于 1958 年 7 月 1 日实施时,联邦已由进步保守党(总理约翰•迪芬贝克)政府执政,并在执行阶段推进各省加入。1966年又由联邦自由党政府(总理莱斯特•皮尔逊)推出并通过《医疗护理法》(Medical Care Act),把医生服务纳入全国性成本分摊框架。到1980年代初(1983–1984),联邦自由党政府(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由卫生部长莫妮克•贝金在1983年12月提出《加拿大健康法》(Bill C-6),并在1984年4月以众议院一致通过的方式确立全国标准;而同年晚些时候上台的联邦进步保守党政府(总理马尔罗尼)又在实施阶段通过部长间协商、解释函等方式推进落地与执行细化。
加拿大的政策史反复说明:很多制度改进并非某党独占,往往是一个党提出、另一个党执行、再由不同党派在争论中修正完善。正因为如此,反毒若坚持非党派,以证据与结果为共同语言,反而更容易形成跨周期的持续改进。如果一开始就被拉进党争、变成“站队”,就很容易把本来可以联合的社会力量分裂掉;相反,坚持非党派、以证据和结果为中心,更能在立法与政策形成的关键窗口期,推动形成可持续的制度改进。
真正的融入:理解制度、参与讨论、用规则推动改进
这也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
在加拿大,多元文化受到尊重,即便语言不通,也可以在某些社区中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但如果因此忽视对主流法律制度、公共政策和政治运作方式的理解,那其实是一种对自身权益的放弃。
真正的融入,并不仅仅是适应语言和生活方式,而是能够理解制度、参与讨论,并在必要时依法表达不同意见。无论是对毒品政策,还是对其他公共议题,这种理性、克制、聚焦制度本身的参与方式,都是民主社会得以不断修正和完善的基础。
世界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政策会调整,政治环境会反复,国际关系也会起伏。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中,个体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对制度的理解和参与能力,而不是对某个政党或某段政治蜜月期的依赖。
当我们批评一项政策,而不是攻击一个政党时,我们不是在“站队”,而是在为一个更理性、更成熟的公共讨论空间负责。而当反毒坚持非党派时,我们也不是在“模糊立场”,恰恰是在把立场落到最坚实的地方:以生命为尺度,以社区为边界,以证据为依据,以制度改进为目标。这,恰恰是民主社会中最重要、也最稀缺的能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