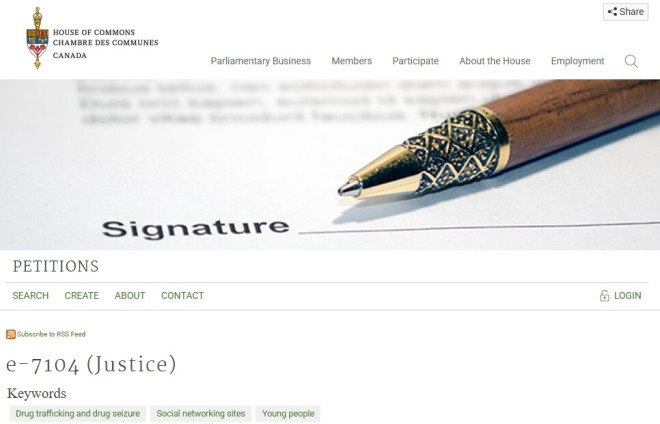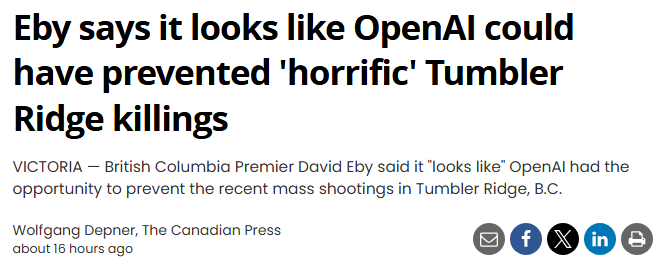二姐,其实并不是我的亲姐姐。
她是好朋友阿蓬的姐姐,我们便随了阿蓬一起,喊她二姐。
那一年,她和姐夫第一次登陆温哥华。人生地不熟,阿蓬托我照应,于是接机、吃饭、看房子,来来回回地忙了几天。后来他们在白石安了家。海边的小镇,街道不宽,风却很干净,吹在人身上,心也跟着慢下来。
再后来,阿蓬的太太阿莲也带着三个孩子过来陪读,姐妹两家住得不远,彼此也有个照应。
阿蓬和二姐夫在国内都有生意,走不开,只能隔一阵子飞过来小住几天。一年到头,聚少离多。我的住处离白石有些距离,平日也不常过去,只有阿蓬飞来加拿大陪家人时,我才顺路去坐一会儿,喝杯茶,说几句话。算下来,七八年的时间,其实并没有见过二姐几次。
可每次电话里,她总是很热情。
“小孙啊,有时间过来玩哈。”
二姐是台州人,说话软软的,尾音常常往下落,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似的。台州话里本就带着一点水汽,说普通话也一样,不急不躁,听着让人心里松下来。我每次都答应着“好好好”,却又一拖再拖,终究还是去得少。
2020年,疫情来了。
一开始谁也没太当回事,后来事情一天天紧起来。学校关了,孩子们在家对着电脑上网课,日子被拆成一格一格的时间表。二姐带着儿子回了上海,本想着暂避一阵子,没想到接下来国内的情况反倒更紧。
小区封控,出行受限,核酸一轮接一轮地做,生活一下子被压缩在几间屋子里。
她在电话里说,小区里很安静。楼道空着,电梯也停了,早晚只听见居委干部用广播提醒大家下楼做核酸。队伍排得很长,大家戴着口罩,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彼此隔得老远,谁也不说话,只是慢慢往前挪。生活物资靠社区分发,连家门都出不去。
2021年,我从阿蓬那里得知,二姐病了,查出来是胰腺癌,已经是晚期。
从那之后,她的朋友圈就再也没有更新过。
以前她偶尔也会发些日常生活:做了满满一桌子的菜,种花、修枝,和朋友出门吃个饭,或者一家人出去旅游。连在门口拍几张枫叶、扫雪,都能开心得像个小孩子。她常常炫耀自己有个巧手的好妹妹阿莲,会做各式各样的点心美食,又会种花种菜,把院子伺弄得像公园一样。
有一天,她忽然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天花板。
白白的一片,什么都没有。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我给她打电话。
她说睡不着,失眠,整夜整夜地对着天花板发呆。
她的声音还是轻的,却明显比以前慢了许多。她说现在的生活就是医院和家,两点一线,哪里也去不了。因为回不了加拿大,儿子已经休学,留在上海陪她。女儿也登记结婚了,可因为疫情封控,连一场像样点的喜宴都没能办成。
有时说着说着,她就哭了。
她说不想再治了,太煎熬。身上总是不舒服,胃口不好,整个人一点力气都没有,白天熬着,晚上又睡不着。她又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儿子的学业,心里过不去,甚至动过“一走了事”的念头。
可转过头,她又说,还想再等等。
等上海解封,给女儿风风光光地办一场婚礼,送儿子回加拿大继续上大学。
那是她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个念想。
那段时间,我常常感到一种无力,像潮水一样,一阵一阵地涌上来。隔着时差和屏幕,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隔三岔五发个消息,或者和她聊聊孩子的近况。妹妹阿莲也回不去看她,一来怕回去后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二姑娘正值中学毕业、申请大学的关键时候;二来当时回国要在酒店隔离,运气不好碰上阳性,还可能被送去方舱,再隔上两周。姐妹俩只能在电话里哭得稀里哗啦。
我也不敢多问她的病情。
只能教她试着做观息法,慢慢地呼吸,哪怕只是让夜里好过一点。我把我当年差点死在西藏的经历告诉她,说实在静不下来,就一遍遍地念观音菩萨吧。
再后来,她的外孙女也出生了。
她亲手抱过孩子。小小的身子贴在怀里,温热又轻。孩子的手指握住她的手,她低头看着,脸上也多了些笑意。她轻轻哄着,陪孩子在阳台上晒太阳,或者在客厅里慢慢地摇着她入睡。
屋子里多了些笑声,也多了些孩子的哭闹声。
日子一下子变得充实起来。
只是,这样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
2022年底,上海迎来了解封。
她也终于圆了那个心愿,给女儿热热闹闹地补办了一场婚宴,送走了儿子。
昨天,我和阿蓬绕着佘山走路。天气还有点冷,天空灰蒙蒙的。走着走着,就聊起了二姐。阿蓬叹了一口气,眼圈有点红,说:
“二姐已经走了整整三年了。”
我一时没接上话,低下头,眼泪毫无预兆地落了下来,落在石板路上。
回程时已是黄昏。车窗外的街灯一盏一盏亮起,又在后视镜里慢慢退远。夜色很深,二姐的面容却一点点浮出来——白石镇的海风里,她站在路边朝我招手;电话那头,她用那种温软的语调说着:“有时间过来玩哈”;朋友圈里,是刚出锅的菜,是花园里新开的花,还有那张空空荡荡、白得刺眼的天花板。
那一整夜,我几乎没怎么合过眼。凌晨四点多,我索性起身,拧开台灯。灯光落在桌面上,铺开一小片暖色。字写了又删,句子摆了又调,像是在把这些年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一针一线地补回来。直到窗外微微发亮,最后一个句点才轻轻落下。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二姐。
梦里还是白石镇的海边。风很柔。她穿着一件素色的裙子,站在窗前,手指轻轻掠过沙发的扶手,动作很慢。阳光从窗子里照进来,把她鬓边的头发映出一层淡淡的金色。她转过身来,看着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像那天第一次去她家见到时一样。
我喊了一声:“二姐。”
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醒来时,天还没亮,枕巾是湿的。屋子里静得很。我躺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回过神来。
2017年,我把房子装修好,正准备添置新家具。和阿蓬闲聊时,他说二姐有一整套欧式家具放在他的公司仓库里,已经五六年了,让我去看看,合适就搬走用。
那是一整套全新的实木家具,客厅、卧室都有。当年他们买下后才发现,放进客厅太拥挤,又退不了货,只好重新打包,放在仓库里吃灰,她自己只留了一张床。
后来我要给二姐钱,她怎么都不肯要。
“你拿去用就好,放着也是放着。”
这些年,每次回国,看到客厅里的那些家具,我就会想起她。那些沙发、柜子、餐桌、椅子,都带着一种安静的存在感,奢华,却不张扬,就那样静静地放在那里。
二姐的微信签名,是![]()
![]()
![]()
![]() 。
。
她其实是个很热爱生活的人。
这样的一位好姐姐,就这么走了。
我甚至没能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
后来再想起她,多半是在一些很普通的时刻。
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家具还在原来的位置。
偶尔,我会想起那句电话里的话——
“小孙啊,有时间过来玩哈。”
她走得太早了,
甚至没来得及
看一眼
二〇二三年的春天。
花儿还在酝酿颜色,
风已经替它们
低低地叹了一声。
日子匆匆,
像一条不肯回头的河流,
把许多尚未盛开的时辰
悄悄带走。
我在忙乱的人间,
一次次错过
花开时
那几不可闻的声响。
于是我想停下来。
哪怕只是片刻——
坐在柔软的草地上,
让大地的温度
透过掌心,
让阳光
轻轻覆上额头,
让风
替我理一理
纷乱的心绪。
不言别离,
只听一朵花瓣
缓缓落下,
落回春天的怀里,
在空气中
留下
一缕
极淡、极轻的
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