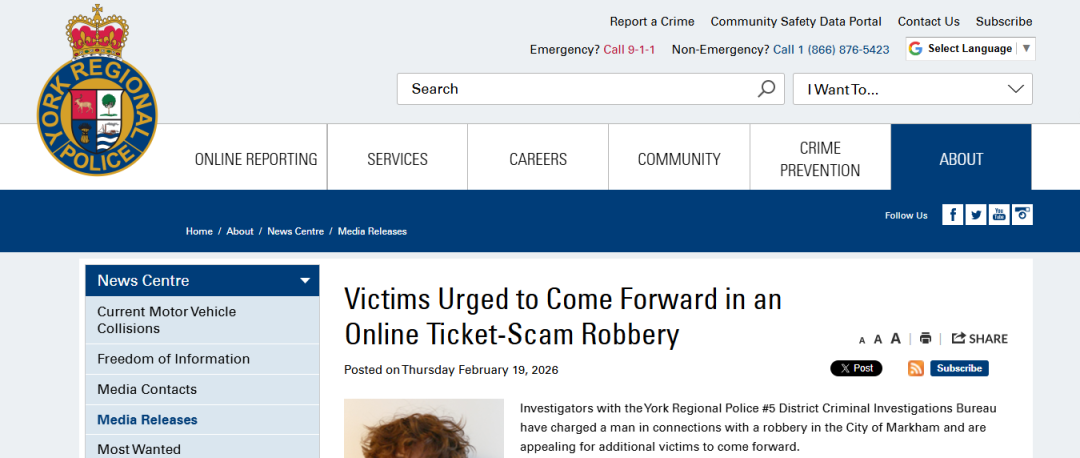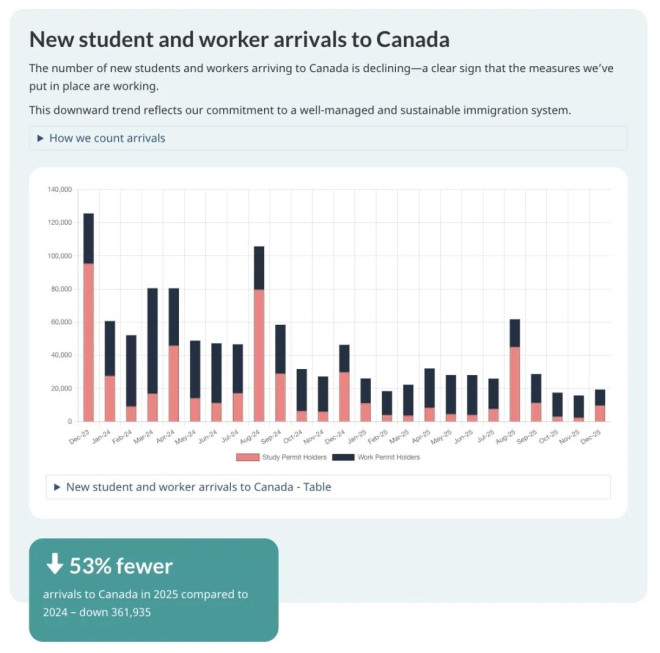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更高明的“盘中盘”,真假难辨,却打动了不少深陷“杀猪盘恋情”的受害者。有的人反而陷得更深,甘愿花钱帮对方“赎身”、逃跑。而在社交平台上,受害者讨论最多的问题,不是“如何要回被骗的钱”“如何让诈骗犯绳之以法”,甚至不是“如何走出被骗的伤痛”,而是“盘哥有没有对我动过真心”。
这两个月以来,我找到了三位“杀猪盘”受害者。她们的经历告诉我,比起被“恋人”骗走几十万,她们更痛苦的是如何面对这段“失恋”。这是“杀猪盘”不同于其他诈骗犯罪的残酷一面:即使受害者认清骗局、感受愤怒,那段“恋情”所带来的情感连接,不会随之消失。她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忍心用“骗子”两个字称呼那个人。
我还找到了两位“盘哥”。此时此刻,他们正在东南亚电诈园区里扮演着“真心爱人”。
其中一位盘哥年仅18岁,却十分老练,假身份、假故事、假情绪价值,娴熟地为比他大几十岁的女性编织一场又一场浪漫幻觉。一旦她不愿意充钱“被宰”,他会用超出年龄的杀伐果断立即拉黑,投身下一段“恋情”。而在远离故土、孤独血腥的电诈园区里,在良心和自我麻痹的拉扯中,在日复一日努力赚取巨额赎身金时,他也会对其中一名受害者念念不忘,因为他从中获取过片刻温暖。
另一位盘哥告诉一位受害者,他每天和不同的女人“谈恋爱”,有时候连他也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在这条生产“爱情”的电诈流水线上,爱与骗的界限时而模糊。金钱、犯罪、复杂的人性纠葛在以下现实中展开。
“杀猪盘”受害者“竹子”提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会怀疑这个人是假的吗?
竹子是中国台湾人。她的LINE头像是一张笑得很灿烂的照片,短发,干净利落,穿着浅色开衫。朋友说那张照片看起来只有40岁,竹子听完很开心,“其实真实年龄至少要往上加十几岁”。
去年五月,她在Facebook上认识了一位男性,对方自称也来自台湾地区。至于他的大陆口音,他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父亲年轻时从大陆去台湾工作,认识了来自台湾桃源的母亲。他出生后,考虑到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父亲又带着他回到了老家长沙,一直生活到他22岁。
他称自己48岁,比竹子年轻一点,在香港上班。他时常发来香港的街景照、冰室的午餐照。竹子去过香港很多次,“那些都是我熟悉的地方,所以我根本没有怀疑这个人是假的。”
在相处的大半年里,他们两三天通一次电话,每次至少半小时,最长的一次聊了两个多小时。他热衷于分享一切生活细节:他说他的小名叫“石头”,家里超生,有人来查时,他就藏到田埂里;他说离异后他一个人带女儿,小姑娘牙齿不齐,叫她戴牙套也不去,竹子还帮他出主意。有一天,他察觉到竹子心情不好,主动关心她怎么了,竹子在电话里哭了一个多小时。挂断电话后,他发来一条信息:听到你哭,我真的好难过,我才知道你在我心中有多重要。
他曾在电话里向竹子表白,竹子以年龄差为由拒绝了。他没有纠缠,也没有离开。一个月后,竹子收到一封很长的书信。
他写道,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久,但我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联结。在信里,他计划着回台湾要做的事,而在每一个计划中,他都提到希望竹子能和他一起。他说,如果你能接受我,我会感到无比荣幸;如果不能,我也会默默地陪伴你。
竹子读后非常感动,在她的成长中,从来没有人和她这么温柔地讲“真心话”。这一次,竹子没有再拒绝他,默认了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
直到竹子发现自己被骗的那一天。竹子想不明白,电诈集团为什么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先制造一场恋爱,再骗走她35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7万元)——这么少的钱?
和竹子一样,马来西亚人阿芝从没想过自己遇到的是一个诈骗分子。去年春天,在日本旅游时,阿芝收到一条Instagram私信,对方礼貌地询问她日本旅游的注意事项。
阿芝点进那人的主页:男性,中年人,喜欢旅游(和她一样),自2013年开始更新照片。阿芝一直认为,所谓的诈骗分子会秀跑车、秀名表、秀肌肉,而他只是一个离异带娃、平平凡凡的打工族。
熟悉之后,他每天给阿芝发早安,问她早上吃了什么,如果阿芝说没吃,他的语气会变得严肃,告诉她吃早餐是很重要的事情。他把每一餐的照片分享给阿芝,一来二去,阿芝也养成了每次吃饭都拍照片给他看的习惯。他还会分享前一晚梦到了什么,在机场给阿芝打电话,背景音是机场的语音播报。45岁的阿芝走到人生半途,乐观独立,待人温和,而所有细节都在向她展示: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懂得关心人的“好男人”。
三个月后,阿芝被他骗走了60万元人民币。
同样被骗的台湾女孩然然事后复盘,说这段“恋爱”比她谈过的任何一段都让她更“上头”。“他给你的情绪价值真的很高,他会跟你说未来的计划。你想一个真正的男人,他怎么可能跟你说未来的事?”一个多月后,然然被这个素未谋面的“男友”骗走近40万元人民币。
相识第3月,那个自称同是中国台湾人的盘哥推荐给竹子一个交易平台。竹子上网查询,是正规平台。她点击盘哥发来的链接,下载了平台,陆续往里面充钱,一共充了35万元新台币。盘哥带着她交易,余额逐渐变成了50万元新台币。盘哥试图游说竹子充更多钱,他说,当本金达到100万时,就能进入更高级的房间,获取更高的收益。这超出了竹子的承受范围,她拒绝了。
盘哥“大方”地帮竹子补足了剩下的50万元新台币。那天晚上,盘哥带着她进入新房间,几次交易让竹子的账户余额翻了好几倍。竹子说,她好像在做一场梦,梦中她拥有很多钱,她的爱人也将回到台湾和她一起生活。
盘哥对她说:你咬咬自己的手指,如果感到疼痛就是真的,不是做梦。
第二天,平台客服告诉竹子,由于你获取的收益巨大,先交20%税金(约60万元新台币)才能提现。“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税金?”竹子第一次对投资平台产生了怀疑。
今年五月初,我在某社交平台上找到了一位盘哥。他的账号IP显示为柬埔寨,发布过几条电诈园相关的帖子。出于媒体人身份,我私信问他是否愿意和我聊聊,聊了几句之后,他说,“抱歉,你勾不起我聊天的兴趣。”
我原以为交流到这里就结束了。几个小时后,他又主动发来信息。他说每次和“客户”聊天神经都绷得很紧,也需要有人说说话。在平台私信聊了半个月之后,他才发来自己的真人版微信。他的最近一条朋友圈是他在KTV喝酒的照片,配文是:“当你一个月能挣十万的时候你就不会抱怨生活的不公。”当他开始信任我时,他终于愿意告诉我他的真名,我用微信转账试着验证,名字和最后一个字一致。他让我叫他“小旭”。
小旭在柬埔寨某电诈园工作,专做“杀猪盘”。一次闲聊时,他告诉我他不喜欢柬埔寨的天气,总是一连就下半个月的雨。他想炫耀自己的“业务能力”,于是主动分享给我一份文件,是他的“养猪”话术包,里面包含六七十条聊天文案,全是小旭自己“创作”的,主题包括情感倾诉、时事政治、投资、星座、个人故事,等等。所谓“养猪”,是指诈骗分子培养和受害者之间的感情和信任。他们将精心策划的剧本、话术包、包含不同场景的图片和视频库视作“养猪”的“饲料”。
最近,小旭有一个很喜欢的丹麦童话“饲料”。故事的主角是王子和邻国公主,他们彼此相爱,公主却被迫嫁给了另一位国王。临别那天,春天刚刚开始,王子送她一束郁金香。王子说,希望我们的感情就像郁金香一样,它会枯萎,也会在明年春天再次绽放。
小旭在话术包里特别标记了这个带着淡淡遗憾的故事。讲完故事后,他还会对那些遥远的女性“客户”说,王子的话也代表我的心。
小旭负责“日本盘”,他的“客户”大多是45岁以上、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日本女人——小旭说,这几年,中国人的反诈意识越来越强,诈骗集团逐渐把重心转移到海外市场。他的人设之一是韩国人,48岁,经营连锁咖啡店,离异,带着一个8岁的儿子。
他发来三张他和客户的聊天截图,对话中,他游刃有余地把控着节奏,装饰着氛围。他对她们说,我已经不再是二十几岁的人了,我想把更好的东西给你,我可以做到。
小旭的真实年龄是18岁。他没有去过日本,也没有去过韩国,因为他没有护照。他是偷渡去的缅甸和柬埔寨。
他每天上班11个小时,用翻译软件同时聊6、7个客户。聊天之外,他用空闲的时间学习关于日本的知识。他看完日本电影《楢山节考》,会记录下电影情节和文化背景;他知道机器猫是川崎市的特别市民;为了让咖啡店老板的身份看起来更扎实,他特地去学了拉花。
为了合情合理地把话题引到“投资”,他前期会进行大量铺垫。在美国增加全球关税时聊他企业的经营成本,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谈俄罗斯停火条件时聊美国的霸权主义,还会聊到日本人熟悉的泡沫经济、“广场协议”、“失落的三十年”。
研究论文《网络诈骗犯罪特点及其预防:以交友诱导赌博投资为例》提到,“杀猪盘”的作案时长跨度在1-6月之间,远超传统诈骗案件的作案时长。犯罪分子极具耐心,和受害人建立亲密关系。小旭说:“其实话术都不重要,每个人都有情感上的痛点,对症下药。”
小旭和她们计划未来,一起煮咖啡,一起去露营。他说他有一只捡来的小狗,叫CoCo,患有心脏病,原主人因为治疗费用昂贵而抛弃它,现在他每个月都要带CoCo去医院。
展露完极富爱心的一面之后,小旭顺势为他的“投资计划”做铺垫:我不责怪抛弃CoCo的人,那人没钱治疗,只能抛弃它,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投资能力,在家人需要我们的时候挺身而出——你得有钱,才能保护好你在乎的一切。
小旭所在的园区管理较为自由,他在上班时间也能用私人手机和我聊天。他告诉我,他是公司里的组长,底下有14个兄弟,大多是刚从国内过去。在他们开单之前,小旭需要负担组员的一部分开支。这些费用算在一起,他还欠着电诈公司56万元。
他只想赚钱,既快又多的钱。一个越南同事开了一票56万美元的大单,让小旭倍感压力。“应该为他高兴的,但是落差感太大,我们正常一个月才几万、几十万,人家一天就比我们一个月都多。”
年仅18岁的小旭用一种冷漠无情地方式处理“杀猪盘”里感情纠葛:他不会在不能给他带来收益的客户身上浪费一秒钟。“(她)不能充钱,哪怕早上‘亲爱的’叫得好好的,晚上就能拉黑。”
在聊天软件上,小旭为千里之外的女性制造着一场又一场浪漫的幻觉:我想我遇见了一位非常特别的人,你和我相似,我们都主动地爱着这个邪恶的世界。
在现实中,当被问到有没有在某一时刻动过心时,小旭说:“不爱,我才18,她们都50了。”
“养猪”之后是“杀猪”。在电诈集团的术语里,这一阶段叫做“点客”。所有的甜言蜜语都是为了“把猪养肥”,顺利进入诈骗流程。
盘哥骗投资的话术,并不总是强调高收益。阿芝的盘哥对她说:“我吃过没钱的苦,所以希望把赚钱的方式教给你,让我们有更多共同语言。”然然碰到的骗局是,盘哥让她下载理财App后转了一大笔钱到她名下请她保管,到了提现时又说他的钱全投在里面,请她先垫付一笔保证金。
然然想,他都肯信任我,把钱放在我的账户里,我垫付一笔保证金又有什么呢?
到这一步,她们已经把盘哥当成真正的的恋人。甚至,在东窗事发后,她们宁愿相信盘哥也是一个上当受骗的可怜人——“杀猪盘”得以施展,并非她们贪财,而是身陷一场虚假恋爱。
被骗之后,竹子仍然没有怀疑那个和她聊了半年的人是骗子。去年10月,她去报警,说遇到了诈骗平台。警察问她:“你没怀疑你朋友骗你吗?”她坚决否认:“是平台骗我,不是这个朋友”。
“最可笑的是,警察问我有没有见过他,我还不敢说没有。”竹子回忆说。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向静访谈过多位“杀猪盘”受害人。她遇到过民警上门20多次劝阻不成功的案例,还有受害人明知被骗了十几万,隔段时间依然心甘情愿地打钱。
“杀猪盘”受害者真正痛心疾首的,不是失去金钱,而是那段看似真实的关系所带来的情感寄托。
然然得知自己被骗40万时没有哭,看到盘哥发来的“对不起”三个字时,却哭了。她说,我相信你有苦衷。
阿芝被骗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都在重复一个动作:拉黑、移除、再加回。因为只有在好友列表里,她才能看到盘哥的动态。阿芝想,他应该也有过片刻真心。在最后那次对话中,盘哥叮嘱她,发生任何事情你都不要自暴自弃。“然后他打了一个视频过来,又挂了,他说本来想看一下我,还是别看了。”
去年六月,阿芝进了一个“杀猪盘”受害者群,群里有100多个人,全是女性。她们在群里聊断联后的戒断反应,聊怎样停止想念。在现实中,她们羞于讲述这段经历,“讲了别人也只会觉得我们人傻钱多”。
旁观者和受害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网络上,有人认为她们“很蠢”“一把年纪了还对爱情心存幻想”,还有人留下评论:“最悲哀的就是,自己也帮着骗子骗自己。”
竹子的信任一直维持到盘哥说他回台湾的那一天。去年10月31日,他发给竹子一张台北101的街景照。“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崩溃了,”竹子说,“他传给我的照片里有一座天桥。”事实上,几年前,那座天桥就被拆掉了。
后来竹子在无数个夜里反刍那些对话时,才发现破绽百出:台湾人从不说“酒店”,而是“饭店”;台湾没有“行长”这个称呼;在盘哥出生的年代,大陆还没有开始计划生育。
竹子给盘哥回了一封信。她斟酌许久,终究没有忍心用“骗子”两个字。她只是委婉地说:“我证实了我的疑惑,也谢谢你这半年以来的陪伴。”
今年端午节,小旭领到了电诈公司发的节日礼盒,里面有几个粽子、一个拼装手办,还有一罐附带说明书的植物种子。他把种子埋进了土里,浇上水,放在办公桌旁,等它发芽。
那天,小旭还是有些不开心。聊天时他对我说:“端午节我妈妈都没有给我发一条信息,她上次和我联系还是过完年。”
小旭出生在贵州,家里有四个孩子,他是最小的。父母从没给他庆祝过生日,连生日是哪一天也没有告诉他,有时候还会忘记小旭到底多大了。“但我是亲生的,长得像。”小旭找补了一句。
小旭很想当一名作家。小学五年级时,余华去他老家做公益,小旭读过《活着》,在互动问答时拿到了余华的签名,他一直小心保管着。
14岁,小旭决定辍学。父母塞给他700块钱,说是让他出去打工。“其实就只够买张车票。”他在国内的建筑工地上扛了两年钢筋,没赚到什么钱,又和女友分手,想换个生活环境,他主动去了缅北电诈园区。17岁回国,被抓进看守所。
当时小旭还未成年,家里只要交两万块钱,就能取保候审,不用坐牢。可他父母不愿意。小旭被判了1年。
小旭对父母的感情很矛盾。有时是恨,他说:“像我们这种人,即使走错了路,也从来不是为自己年少无知买单,是为父母买单。”“如果可以,谁愿意出生在一个没钱又没爱的家庭。”有时,他又帮父母找借口,说他们只是没文化,不知道怎么对待自己。
18岁出狱后,小旭用身上最后的400块教了一笔网课学费,学习在某网站上发文章赚钱。总共赚了40块。然后,他再次南下,进入柬埔寨电诈园。他说自己“走投无路了”。
小旭只花了半个小时,就讲完了他的成长经历。他调侃道,原本是上大学的年纪,现在却在东南亚“上大学”。他每天在北京时间8:30起床,他经常7点才睡着。他说他舍不得睡,因为“只有夜晚是属于一个人的自由时间,不用去伪装自己,扮演一个成熟的人”。
他说:“我这种人,不用去同情,也不值得可怜。”
另一位身在泰国的盘哥“洋葱”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做这个行业的人,一点都不值得可怜。”洋葱的上一份工作是在缅甸给一个大哥当司机。大哥是他老乡,干的是不干净的生意。洋葱也学会了吸毒、赌博。赚得钱不够花了,去年年初,他主动去了泰国的电诈园区。“没学历,没本钱,就做这个碰碰运气,运气好,一下就起飞了。”
洋葱负责欧美市场的电信诈骗,他的主要人设是“投资专家”。他每天工作16个小时,日夜颠倒,周末下班可以出园区,过年能放两三天假。进园区一年半了,洋葱说他还没开过一单,也没挨过打。他每个月拿8000元人民币底薪,交1000元保护费,剩下的只够基本生活开支。他说园区消费和抢劫没区别,一份普通的土豆牛腩盖饭卖50块人民币——园区外,一顿简单的泰国本地午餐还不到15块钱。
洋葱的室友八个月赚了40多万,没有给老婆孩子寄过一分钱,全拿去赌博了。另一个朋友每年至少赚50万,钱一到手,几小时后就赌得身无分文,他老婆说想带孩子去泰国见他,他说没钱。我们聊天时,洋葱收到朋友发来的信息,说赌钱输光了,让他送5万泰铢去赌场。
在缅甸时,洋葱交往过一个当地女朋友。洋葱说,女友对他算不上真爱。他带她去当地最贵的餐厅吃饭、最奢华的酒店开房。送女友金吊坠的时候,洋葱发了两个款式让她选。她问他:哪个更重?
上个月,洋葱找了一天周末,去见一个之前认识的按摩女郎。临走时,他留了5000泰铢给她——在网络上,他们用甜言蜜语为陌生人编织被爱的幻觉,在生活中,也只能用金钱交换陌生人的片刻陪伴。
被骗之后,竹子和然然都主动结识了其他盘哥,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帮助自己从痛苦中走出来。一个盘哥告诉竹子,园区招人有成本,从国内过去的新人一进去就欠公司钱。如果业绩好,几个月能还清,有机会回国;一旦开不了单,欠款越滚越多,回家也遥遥无期。然然则想起,在坦白局时,她问她爱上的那个盘哥:你开心吗?对方立刻回复:不开心。
今年端午节,小旭领到了电诈公司发的节日礼盒,里面有几个粽子、一个拼装手办,还有一罐附带说明书的植物种子。他把种子埋进了土里,浇上水,放在办公桌旁,等它发芽。
我和小旭交流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是我的生日,小旭突然说,我们聊了这么久,想送你一束花。我说等到下次生日吧。他说,“当下就好,别留在以后。”他的工作话术包里也有一句类似的话:我们要像珍惜礼物一样珍惜今天。
“杀猪盘”不同于其他诈骗形式,盘哥总是花很长的时间搭建关系——哪怕是假的,但如果他们在某一刻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关心、陪伴,在实施诈骗行为时,他们会感到哪怕一丝的良心不安吗?
小旭不再有任何自我谴责。他异常冷静地告诉我:“每个人的心狠程度都取决于他当下的状态。”
而在我们认识之初,我问小旭是否愿意分享他的故事时,他说:“你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另一位盘哥的回复是:“你会关心我的生活吗?”这让我意识到,他们并非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地活着。远离故土、孤独血腥的园区环境、随时可能降临的司法审判、道德叩问和自我麻痹,他们的内心注定无法平静。
小旭订的那束鲜花里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不是坏人,只是生活让我不得不选择这样的道路。”但小旭大概也很清楚,终有一天,他会面对法律的制裁。“得到一些本不应该属于你的,肯定就要付出。”
按202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国务院、公安部门等会同外交部门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有效打击、遏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杀猪盘”参与者也将因诈骗罪受到司法审判,最低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最高可判无期,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在柬埔寨做生意的中国人沈星星,2023年跟一个朋友参观过当地的一个电诈园区。他记得很多人的身上有明显的伤痕。“那种不讲规矩的公司,(他们)今天被卖到这里,明天又被转手到另一个地方。”
沈星星的那位朋友负责从国内招聘电诈人员,再卖到各个园区。这位朋友经常殴打员工,人手不够的时候,直接去别的公司抢人。朋友得罪的仇家太多,客死他乡。沈星星一路追查,最后发现是朋友的一个手下买凶杀人。
去年,沈星星决心离开柬埔寨。回国前,他在东南亚旅游,路过一片海滩,看到有人在沙滩上写下两个很大的字:“中国”。沈星星猜测,可能是某个异乡人想家,但是回不去了。这让他想起另一件小事。今年初,当中国第六代战斗机试飞成功的消息传到柬埔寨电诈园区时,里面的人燃放烟花为祖国庆祝。“你说他们到底是爱国,还是不爱国呢?”闯荡东南亚五年了,沈星星依旧对人性的复杂感到困惑。
东南亚国家横跨三个时区,有四个标准时间,园区里的人员负责的盘口不同,又有各自对应的工作时间。但他们还是不约而同地过着北京时间。“习惯了。”洋葱说。
去年,小旭在看守所过了18岁成人礼。今年,他特别想为自己过一个像样的生日。他请兄弟们去了电诈园区里的商务KTV。他发给我那天的消费账单,账单上,一听可乐卖5美元,一位越南佳丽标价300美元。一晚上,小旭花了将近70000元人民币。
吃蛋糕时,小旭只许了一个愿望,希望家人平安。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第二天睡醒,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没有发来祝福。他把全家人都拉黑了。在柬埔寨的这段时间,他帮三姐还了四万多网贷,转账给没钱吃饭的大哥,家人过生日,他一一送去红包和祝福。
小旭偶尔会提起他的第一个“客户”。虽然他否认自己对她动过心,但他说就像人总是对初恋念念不忘一样,他在那场“恋爱”中第一次感受到“恋人”的关心。两年多过去了,他偶尔还会想起她。小旭记得她的英文名(字母R开头),1982年出生,住在日本名古屋。
洋葱说,很多盘哥都会爱上某个“客户”。“有一个(盘哥)回国后,从陕西去四川奔现。那个‘客户’躲起来偷偷看盘哥长相,然后直接拉黑,转头走了。”
他们在挣扎中欺骗,也在欺骗中继续挣扎。一个IP定位在柬埔寨的账号写道:“来到这个鬼地方,我把我最优美的语言、我最真诚的爱都给了我不喜欢的这些女人,真是唏嘘。”

阿芝的盘哥曾对她说过:“和你聊天有时候自己都被感动了。”阿芝当时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后来才理解他的意思——他每天要和好几个女人“谈恋爱”,说着浪漫又温柔的话,有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是演的,哪些是真的。
阿芝退出了之前加入的杀猪盘受害者群。她决定向前走,“不能一直沉溺在怨恨里”。
在寻找受害者的时候,我关注了一个叫“猪妹”的账号。在近百条笔记中,“猪妹”写下了她所了解的电信诈骗产业链的细节,包括各个园区的作息时间、体罚方式、销冠盘哥的话术包,以及从园区赎身的赔偿金额。她告诉其他受害者,21天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只要撑过21天,就能停止对盘哥也是施害者的想念。
去年年底,“猪妹”停止了更新,并在主页隐藏了那篇《我和一个猪仔的爱情故事》。在最后一篇笔记中,她说打算回归正常生活了。
竹子和盘哥已经断联八个月了。她比以往更加频繁地更新Facebook的动态,她想告诉那个人,自己没有被生活打倒。竹子说,如果未来某天他还能出现在她面前,她会送上一个大大的拥抱,因为这代表他已经勇敢地走出了黑暗。
就像她在告别信里写道:我希望你有一天能够站在阳光下重新生活。
应对方要求,文中竹子、阿芝
然然、小旭、洋葱、沈星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