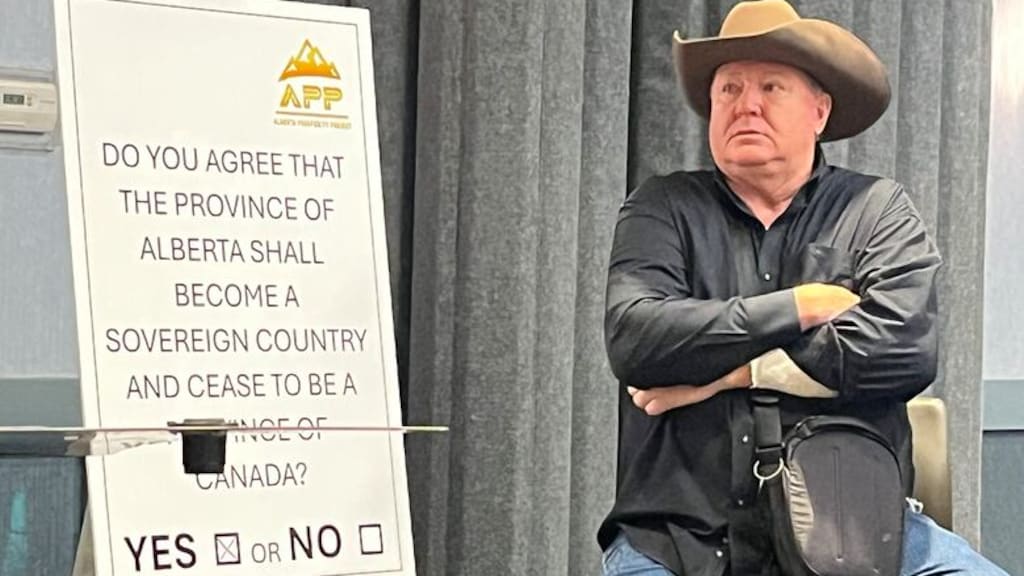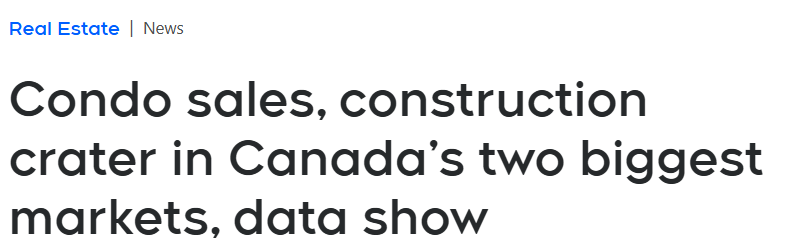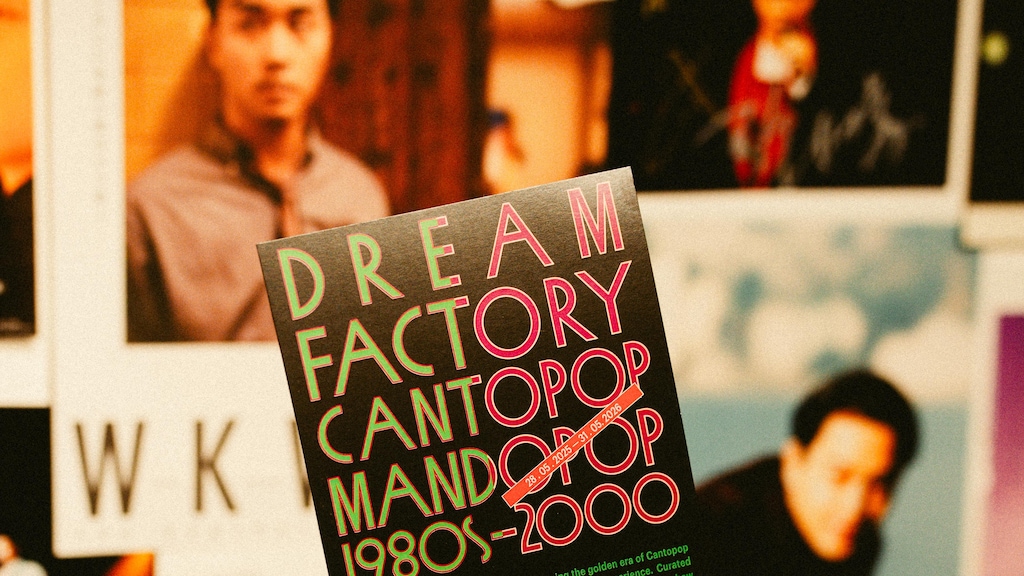今年24岁的小舟,目前是加州一所顶尖大学的大二学生。回顾成长历程,他形容自己走得并不顺利,「我感觉自己根本没有家,像一只流浪狗」。

小舟出生于美国,但在两个月大时就被父母送回中国江苏,由祖父母代为抚养,一直到八年级才回到美国生活与读书。在中国那段时间,他受到长辈的疼爱,几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祖父母生怕他哭闹,无条件地顺从他的需求。但这样没有限制的溺爱,并未为他创建规范和自律,反而让他在回到美国后,遭遇一场巨大反差。
与父母久别重逢,小舟发现彼此之间像是两个世界,他形容父母冷淡而严厉,经常批评他不懂事,却没有人真正教他该怎么适应这个家,他无法理解父母,也无法融入学校生活。语言不通、文化隔阂,加上亲子关系的距离,让他成绩始终不佳,靠打电动游戏打发时间,情绪低落。
勉强从高中毕业后,他进入社区大学,期间一度因抑郁症休学一年,几乎跌入谷底。直到心智逐渐成熟,他才慢慢拉回自己,最终成功申请进入名校就读,「有时候我会想,爸妈是不是不要我了?从我还不会讲话的时候,他们就把我送走了。」
卫星宝宝 移民家庭普遍
在美国,每年都有华裔父母选择将刚出生的婴儿送回中国托亲人照顾。这些孩子返美时,几乎不懂英文,听不懂课堂内容,无法与同龄人交流;再加上与父母多年分离,亲子关系疏远,信任与沟通困难重重,常在学校感到孤立,成绩也多半落后,语言障碍与文化冲击双重夹击,使他们在课业与心理层面皆面临挑战。
慈济纽约合心区教育干事秦惠仪指出,疫情后,慈济与布碌仑160小学合作的课后辅导班中,最初有超过一半的孩子是「卫星宝宝」(satellite babies),这些孩子多半在入学年龄到来后才返美,但往往难以衔接语言与课业,适应过程艰辛。
纽约亲子互助会创始人黄妮可指出,协会自2016年成立以来已有1000多名会员,其中一半以上的孩子都是卫星宝宝;这一现象在来自福州的移民中尤其普遍,几乎身边的亲友都曾在孩子出生后将其送回中国照顾。
亲子互助会的创始人伍Iris表示,许多华裔无证移民偷渡来美后,只能蜗居在多人合租的出租屋内,身背巨额债务,无法提供孩子良好的生活环境,「把孩子送回中国,都是无奈之举」。

早期分离 酿成负面问题
麻州大学(UMass)医学院助理教授苏少冰是首位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经费、专门研究华人社区「卫星宝宝」问题的学者。她希望通过社区数据支持申请更多资源,帮助这些子女健康成长,同时协助不得已将孩子送回国的父母,理解如何正确教养,减少早期分离带来的负面影响。
苏少冰表示,在针对24个「卫星宝宝」家庭的访问中,许多孩子在返美初期出现吃不好、睡不好、拉肚子,甚至大小便失禁等退化现象,受访家庭普遍提及孩子常有咬人、伤人或无故哭闹等行为;她补充,部分孩子进入青春期后,情绪暴躁、难以控制,或伴有沉迷电子产品的现象,「沉迷虚拟世界,是因为对现实世界不满」。

亲子断裂 伤害难以挽回
黄妮可提到,亲子疏离造成的问题十分严重,有些家庭最终酿成悲剧,例如布碌仑8大道母亲李林溺毙两岁女儿的案件,也有不少孩子青春期心理问题频发,出现打架、斗殴、自残等行为。
伍Iris认为,许多家长将孩子的教养问题完全归因于孩子本身,例如当孩子被诊断为多动症,只让他吃药,甚至过度责骂,却从未反思是否与早期的亲子分离有关。
苏少冰指出,早期分离容易造成孩子缺乏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在她的研究中,有经过早期分离的受访者表示,她们在青少年时期仍需父母陪伴才能入眠。她呼吁家长不要只看表面的行为问题,而应回顾孩子的过去,理解那段缺席的影响,为孩子提供稳定而有安全感的成长环境。

只要改变 就有修复可能
黄妮可分享了一名协会成员的故事,她指其中一名孩子在幼时被送回中国由亲友照顾,步入青春期后被诊断出严重抑郁症,从小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因为父母有了第二胎,她认为爸妈更爱妹妹,「妹妹是妈妈带大的」。
然而,她的母亲个性开朗,愿意配合学校与医疗团队的治疗,主动参与家庭辅导与活动,参加社区活动;随着交互逐渐创建,孩子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情绪稳定下来,学业也开始进步。
秦惠仪指,除了课业成绩,家长也应重视德行与情绪教养。在慈济的课后班中,通过品格课程与情绪教育,许多经过与父母早期分离的学生,学会了与人相处、表达感受,也逐渐找回对自己的信心。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运行总监沈卉指出,社区对于卫星宝宝的支持资源仍然不足,亚裔常被视为「模范族群」,实际上却面临语言、心理与家庭教养的多重困境。她呼吁政府重视移民家庭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提供双语服务与文化适应资源,协助他们平稳过渡,「家长的角色无法被替代,唯有增加交互与理解,才能修补那些错过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