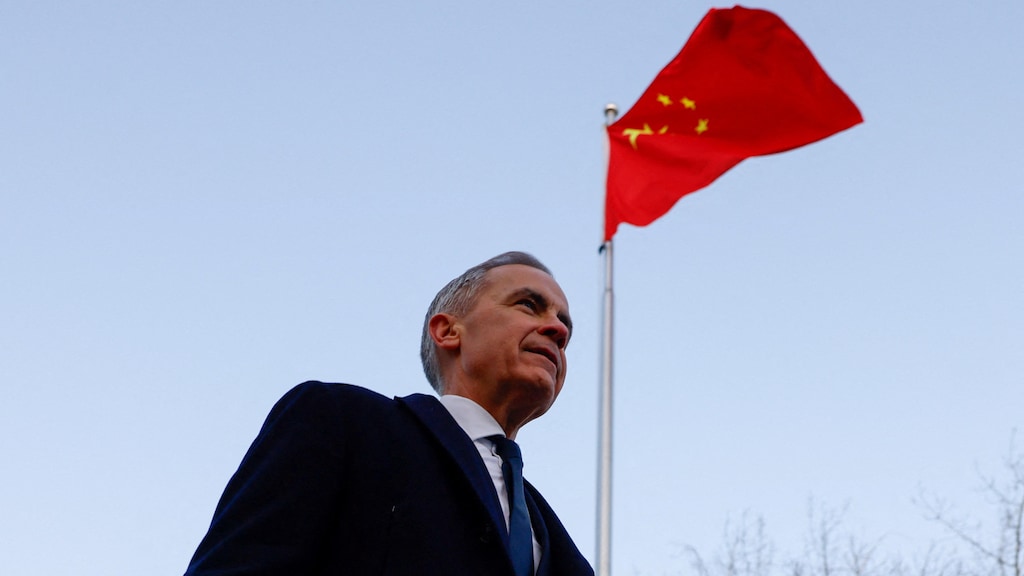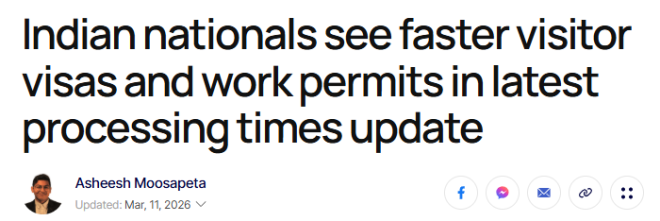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日前刊登了Tony Keller的专栏。以下是他的自述。
1985 年春天,在我 11 年级毕业前几个月,我申请了一份在一家墨西哥风格餐厅打工的暑期工作,店家地点离我家不远,位于蒙特利尔West Island社区。这家餐厅需要招聘几十名服务员、厨师、洗碗工、以及我应聘的杂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学生,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周围的社区。
第二年,我到了可以卖酒的年龄,很快就被另一家餐厅聘为服务员。接下来的几个夏天,我在三家不同的连锁餐厅工作,最后一家是Red Lobster餐厅。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尊重他人的技能。我一直被谬赞为好学生,但在为客户服务的现实世界里,我的表现却是垫底的。我无法同时接待四桌以上的客人,所以我的工友们赚得比我多,经常一晚上就能拿到 100元的小费。如果算上通货膨胀后,相当于现在能拿到 225元小费。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听过很多加拿大家长分享他们的经历,说他们上大学的孩子找暑期工有多难,或者说他们即使寄出了几十份求职申请表也没有找到一份暑期工。
相比之下,我不记得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找暑期工作时遇到过什么困难。是我看事情过于乐观(rose-tinted glasses)?还是现在的孩子们都是一群装模作样的逃避工作者(job-shirker)?
答案就在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中。
8月份,15 至 24 岁的在校学生中有 16.5% 没找到暑期工作。加拿大有将近 290 万名在校学生(意为秋季还会继续上学),有暑期工作的比例仅为 49%。
被统计局称为“其他学生”的群体(意为秋季不再继续学业,或不确定是否返校的学生)的情况更糟。8月份,他们中80%的人加入了劳动力大军,这意味着他们愿意并能够工作。但有 20.1% 的人没找到暑期工作。
这些数字都比去年夏天或前年夏天糟糕,也比疫情之前糟糕。2019年8月,学生未找到暑期工作比例比现在低近 4个百分点,而就业率则高出 6 个百分点以上。
而在 1988 年8 月,当我还在Red Lobster餐厅打工时,返校学生的未找到暑期工作比例仅为 7.8%,不到如今的一半。能找到工作的比例为 64.6%,比现在高出 15 个百分点以上。
更重要的是,这些官方数据很可能低估了两个时代之间的差距。这是因为放弃找工作的人不被算作未找到工作者。他们被记录为脱离劳动力大军。低失业率往往会吸引人们加入劳动力大军,但工作机会的缺乏会打击想尝试工作的学生和年轻工人的积极性,从而将他们中的一些人挤出劳动力大军。
1988 年的夏天在很多方面与如今年轻人的经历正好相反。
我是婴儿潮之后生育低谷(baby bust)时期的一员。在校学生所代表的入门级劳动力队伍正在缩小。这使得当时成为入门级劳动力的时机相当不错。
据统计局估计,1986年至1988年夏季,15至24岁的在校学生和年轻工人人数减少了25万多人。最后一批“婴儿潮”一代逐渐走上更高级别的工作岗位,取而代之的是人数更少的“X一代”。
而在过去两年中,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5至24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了 50 多万,新移民贡献了大部分人口。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暑期工作,部分原因是当时年轻人不够用。年轻的我成为香饽饽,这正是如今的入门级劳动力所不具备的。
我的好运是个意外。他们的坏运气至少部分是联邦政策故意造成的。
有问题的不是移民政策。在我学生时代,加拿大接纳移民的水平低于现在,但仍高于大多数同类国家。1991 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6% 的加拿大人口出生在海外,这一数字依然高于现在的美国,也高于美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至少可以追溯到 1850 年。
在我的社区、学校和暑期工作中,也有许多孩子是移民或(像我一样)移民的子女。
不同的是,墨西哥餐厅、Red Lobster餐厅和周围所有其他餐厅或商店当时都没有招募临时外劳计划。也没有交学费就能拿工作签证的“野鸡大学”(puppy-mill college)。我们这些本地孩子是唯一的入门级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