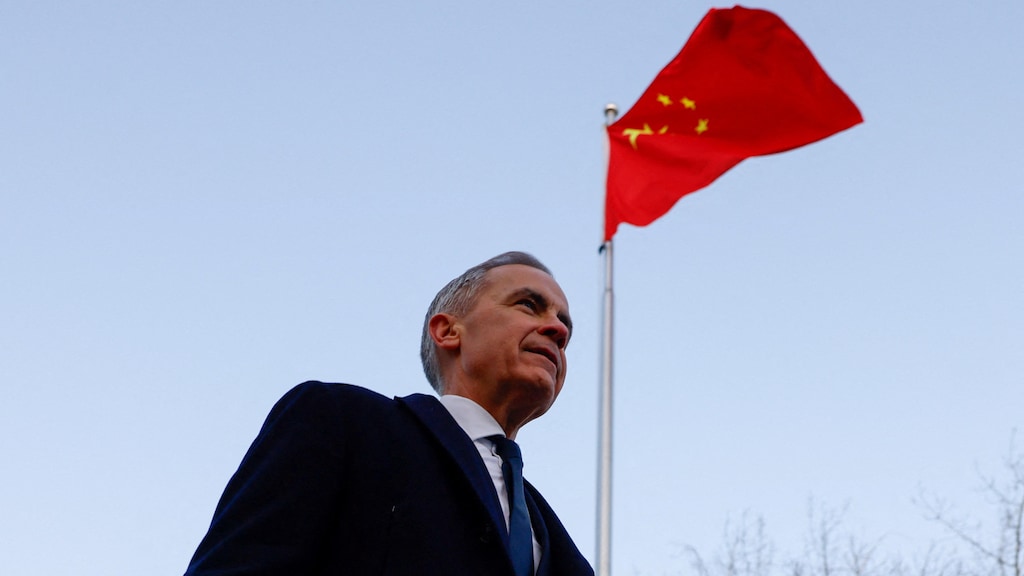安格拉·默克尔最喜欢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部歌剧感情丰沛而复杂,讲述了一个至死不渝的悲剧爱情故事。
剧中如此有张力的情绪,似乎和她本人很不搭调——执掌德国政坛16年后,与她深度绑定的关键词是沉稳理性。
在如今强人政治的时代,政客们忙不迭地展现个性,以有别于内敛克制为傲,随心所欲表达,有时甚至不计后果。默克尔反而像异类。她不喜欢煽动的语言,也不喜欢外露情感,几乎不会在公众场合被看到有情绪波动。
但她并非始终如此,私底下的默克尔喜欢谈天说地,刚当上总理时,她甚至还会模仿会晤对象暗讽其缺点,不论对方是教皇还是法国总统。如今的审慎特质部分源自她的性格,也源自30年从政经历的形塑,毕竟从政之初,默克尔曾因某些言论招致不怀好意的指责,她憎恶这种用心险恶的意气之争。
虽然早已熟稔于隐藏情绪与好恶,被称作“铁娘子”的默克尔也有过眼中噙泪的时刻。去年年末在联邦议会讲话时,她双手合十,几度哽咽,言语恳切地请求民众遵守防疫规定,在圣诞节期间减少非必要接触,“我很抱歉,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抱歉。如果我们(为假日)付出的代价是每天有590人死亡,这绝不可以接受。”
彼时,德国正承受第二波新冠疫情的冲击,日增确诊病例一度超过3万例。德国没能复刻第一波疫情到来时的优秀应对,不够严格的封锁政策导致感染率高企,默克尔也因此饱受批评。尽管这不能完全怪罪于总理——德国16个联邦州各自制定公共卫生政策,默克尔无权干预地方决策。
这位量子化学家出身的总理只能循循善诱,试图以一贯的理性作风说服民众遵循科学指导。效果自然是有限的,民众对长期的封城感到疲倦,这让默克尔在演说中罕见地表现出感性一面。
对默克尔来说,这是她在总理任期面临的又一次危机时刻,也是最后一次。早在2018年10月,她便宣布不再参选德国执政党基民盟(CDU)党主席,且将在第四个总理任期届满后卸任。尽管那时,她不可能预见到任期尾声会面对如此大的疫情挑战,但应对危机似乎成为其总理生涯的主线故事。
像每个至暗时刻一样——无论是2007年的金融危机、2009年的欧元危机、2015年的难民危机,还是眼下的气候变化以及新冠疫情,这位出身于前东德的女性政治家总能挑起德国乃至欧洲的大梁。
通过欧债危机走到欧洲前台
瓦格纳的另一部歌剧《尼贝龙根的指环》也备受默克尔的喜爱,它同样是一个关乎命运的作品。默克尔对这部歌剧的评价是,“如果事情一开始就错了,反而可以成就某些人,但永远都不会回到好的结果上来。”
在《默克尔传》中提及总理的这一爱好时,对她颇为熟悉的作者斯蒂凡·科内琉斯(Stefan Kornelius)形容,“起步对,步步皆对”正是默克尔的人生座右铭。她习惯于从结果开始思考事情,并以学者的严谨态度对问题进行分析评估,尽可能搜集事实,在逻辑架构内权衡出解决方案。
这也带来了默克尔做决策时的一大特点——不拘泥于党派之别,以务实为根本。
2005年击败寻求连任的社民党人施罗德后,默克尔开启了第一个总理任期。尽管她来自中右翼政党基民盟,却沿袭了施罗德经济改革方案“2010议程”的理念,采取减税、削减补贴等举措,使政府财政赤字与社保支出显著下降。
金融危机之时,德国遭遇了不小的冲击,2009年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现过5.57%的负增长。但紧缩政策帮助其快速走出阴霾——直至新冠疫情暴发前,德国经济连续10年实现增长,失业率降至2019年的3.1%,政府财政空前盈余。
然而,在默克尔上任那一年,德国的失业率高达11.3%,为两德统一以来最糟糕的时刻。自她上任开始,德国经济实现复苏,摘掉了“欧洲病夫”的标签,也免于被裹挟进席卷南欧的债务危机泥沼。
彼时,希腊、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却债台高筑、财政状况岌岌可危。2009年,希腊新政府宣布其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超过12%,这远高于欧盟允许的3%上限,欧元区的巨大危机开始彰显。很快,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陆续出现问题,并要求援助。
危机最初,默克尔并没有主导解决问题的意向,无条件为这些国家提供援助绝非德国所愿,在德国人看来,希腊应该自己承担起责任。但保守旁观的姿态引发其他国家不满,欧洲一体化带来的紧密联结也难让德国置身事外。
德国经济实力出色,其领导力不可避免外溢到政治领域,并被推到欧债危机处理前台,扮演起“不情愿的霸权角色”。
默克尔的解决思路是“节约”。她力主希腊等受援国采取紧缩政策,控制政府支出,只有这样才能挣脱债务陷阱、培养经济竞争力,一味援助不仅无法遏制危机,还将拖累欧洲其他国家。简而言之,只有施行改革才有钱拿。
这是正确的逻辑,但也是难被接受的方案。紧缩意味着痛苦改革,“债务刹车”将限制刺激经济增长,也无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最初,这样的方案几乎被所有人视为灾难,默克尔则成为风口浪尖上最遭恨的那个人。她被攻击是“又一个希特勒”,在政治漫画中频频遭到丑化——当她去希腊、西班牙等国访问时,不断有抗议示威者涌上街头。
尽管默克尔曾透露,她并不想推行如此强硬的经济政策,也不想做这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无疑,她还是坚决遵循“起步对、步步皆对”的原则,而在欧债危机之中,保护欧元、让希腊留在欧元区是最重要的前提——被隔绝在柏林墙东侧多年的默克尔是欧洲一体化的信徒,她也致力于让欧盟经受住全球化竞争的考验。
默克尔相信理性推演的必要性,她不轻易松口,总是迟迟不做决策,可以有妥协,但不在深层信仰上让步。在德国的推动下,受援国最终接受了默克尔的“节约”方案,欧洲还为此设立了总额为5000亿欧元的永久性援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德国在其中承担了26.96%的最大出资份额。
欧债危机之后,默克尔不再是某一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当这个全球最富裕的地区遭遇挑战时,她都是最重要的掌舵人。只不过,基于她在希腊债务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德国与欧洲的关系生变。随着德国政治影响力的上升,批评与敌意也纷至沓来:德国是否在将自身意志强加于欧洲?危机吞噬穷国时,德国是否坐收渔翁之利、以低税政策网罗人才?
但无疑,德国与欧洲是彼此缠绕的共生关系。2009年在洪堡大学发表演说时,默克尔将欧洲政治解释为德国内政。她也曾说,“德国一直视欧洲统一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这一信念深深体现在其任期始终。
尽管德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傲视欧洲,但过去十年,决策上的相对保守使默克尔政府没能及时推动国家的改革与创新。技术领域遥遥领先的德国,在数字化时代远远落后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甚至在欧盟内也未能占据鳌头。
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2020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DESI)”,德国在欧盟27国以及英国当中排在第12位。而在七国集团(G7)国家中,德国的数字化水平处于倒数第二,仅仅高于意大利。
直到2019年,德国终于决定做出改变。默克尔高调提出“德国需要一个全新的产业政策”,以应对来自亚洲不断增长的竞争势头,并意欲在欧盟层面继续推动“欧洲新产业政策”的主张。
气候议题上展现出激进一面
欧债危机的处理中,默克尔表现出的不仅是强硬,也有愿意为了达成一致而妥协的姿态。这种特质,最早可以追溯至1995年的柏林气候峰会。
那会儿气候变化还是相当新鲜的议题,三年前的里约峰会上,各国一致同意气候政策是全人类的问题。可要如何兑现《里约宣言》的内容,并在不同国家和利益群体间取得更多共识、制定出对下一阶段气候政策具有约束性的任务,并非易事。
时任德国环境和核能安全部长的默克尔受命主持了这场长达11天的峰会,她在不同阵营之间穿梭调停,避免讨论失控。会议结束后,默克尔说,“只要能让事情向前迈出一步,就算知道不会得到一致掌声,我还是会去做。”
科内琉斯对默克尔的理解是:她不知教条主义为何物,最爱运用平衡、传达与妥协的主持风格,不需要太多冲突就能得到结果。
最终,柏林会议通过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履行公约的决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116个缔约方同意立即开始谈判,就2000年后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保护气候进行磋商,以期最迟于1997年签订一项议定书,这正是之后的《京都议定书》。
这是默克尔在国际外交上的一次成功试水,也正是在这个职位上,她开始投入减碳工作、关注能源问题,还在《科学》杂志撰文阐述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
就任总理后,气候也成为默克尔政府的重要议题,看似保守的她时常展现出大刀阔斧的激进一面。
今年4月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时,默克尔说,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与1990年相比已经减少了40%,并计划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到次月时,德国再度加码,计划提前五年实现该目标。
这不仅因为默克尔在气候问题上很在意代际公正,也有着更为现实的考虑——此时距离联邦议会选举还有5个月,民调显示,气候变化是德国选民最关切的问题之一。而在环保与气候议题上最为激进的绿党势头尤劲,支持率达到28%,远超执政党联盟党的21%。
顺势而为同样体现在默克尔淘汰核能的决定中。2011年福岛核事故之后,默克尔政府逆转其能源政策,决定在2022年前关闭所有核电站,这完全违背其2009年连任竞选时延长核反应堆寿命的承诺,但默克尔依然推进了这个极具绿党特色的决定。
这个主张看似大胆,却有着深刻的民意根基。福岛核事故后,德国选民对于核威胁的担忧迅速反映在选举之中,基民盟首次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被绿党超过。对于默克尔而言,这是能源政策必须改弦更张的信号。
但舍弃核能,也意味着德国在彻底实现能源转型前不得不依赖煤炭、天然气等能源,这让“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成为影响欧洲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据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官方社交账号消息,该公司董事会主席米勒9月10日宣布,“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已完成建设。此前项目施工方发声明说,随后项目将进行调试,以便在今年年底前投入运营。
这条全长123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于2015年启动建设,目的是将俄罗斯的天然气经由波罗的海送到欧洲多国。建成之后,俄罗斯对德国的天然气出口量将翻一番。德俄两国不仅是最大受益方,两国的捆绑也会更为紧密。
但这个项目被认为将乌克兰的地缘安全置于危险之中。在此之前,俄罗斯天然气需经由乌克兰输送至欧洲,乌克兰可以从中获取数十亿美元的过境费用。新管道的出现不但会给乌克兰带来经济损失,也使其地缘重要性下降,本就在乌东地区与俄罗斯冲突不断的乌克兰将更难与之抗衡。
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亚太区负责人何彼得(Peter Hefele)向“全球报姐”指出,鉴于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冲突,德国40%的天然气资源却要依赖俄罗斯,这并非负责任和明智之举。
“‘北溪2号’会让中东欧国家担忧自己被边缘化,如果要讨论欧洲统一的能源政策,德国应该与邻国达成共识再做决定。”致力于研究经济政策和能源气候等议题的何彼得说。阿登纳基金会于1964年成立于德国波恩,是由德国政府设立的两大非盈利性基金之一,隶属于基民盟。该基金会在北京和上海均设有办公室,旨在促进中德在学术、经济、科技和社会等领域的交流。
凭借巨大的天然气工程,俄罗斯将扩大在欧洲的影响力,这让美国如鲠在喉。美国政府称,欧洲将在能源市场上被俄罗斯所控制,并威胁将制裁“北溪2号”相关实体,同时施压欧洲相关国家领导人不要配合该项目建设。
尽管争议与压力不断,默克尔始终决心力保“北溪2号”平稳推进。8月赴俄罗斯进行“告别访问”期间,“北溪2号”也是默克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时的讨论重点。在此之前,默克尔已经成功争取到美国不再阻挠该项目的承诺,但双方达成的协议亦规定,一旦俄罗斯试图将能源供应当作武器,德国将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系列措施,以限制俄罗斯在能源领域向欧洲出口的能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向“全球报姐”分析称,“北溪2号”并非如默克尔所说仅仅是个商业项目,它是俄欧之间能源关系保持稳定的基础。“在和有冲突和分歧的国家进行交流时,德国要找到与之继续合作和对话的纽带,这样双方关系才是可控的。”
接纳难民酿成最大执政危机
对于危机,没有什么应对政策能让所有人欢迎,但向难民敞开欧洲大门,制造的不仅是争议,也是默克尔执政生涯最危险的挑战。
除了对其执政地位造成撼动,接纳难民给德国和欧洲带来的政治后果再清晰不过——民粹崛起、排外主义盛行、极右翼势力逐步吞噬建制派的选民根基。
无从得知是什么支撑着2015年的默克尔顶住批评、坚持难民政策。或许因为在东德三十多年的生活让她对迁徙自由格外珍视,也或许如荷兰前首相吕贝尔斯所说,默克尔是坚定的路德宗信徒,“这件事关乎其内心深处的道德信念”。
◆2015年默克尔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但当今年8月阿富汗局势陡然生变,又一次人道主义危机来临,默克尔并没有重复六年前的选择。她表示,无意接纳大量阿富汗难民,德国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但会为阿富汗的邻国提供援助。
如果以“起步对、步步皆对”的逻辑理解六年前的默克尔,她同意大量难民进入德国不仅出于塑造人道主义的国际形象,也是希望外来者可以填补德国短缺的劳动力市场。
默克尔再三强调“我们能做到”,德国民众还在火车站迎接被匈牙利等国拒之门外的难民,“欢迎文化”的景象一度看起来很美好。但
现实走向很快背离了她的预期,来自德国内部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反对声不断——由于多国不愿配合默克尔的政策,涌向德国的难民数量超出想象。
2015年10月的一次民调显示,44%的民众认为移民对德国弊大于利,较前一个月上升11%,对接纳难民持积极态度的比例为35%,下降了10%。而在2016年新年夜,科隆火车站发生大规模性侵与抢劫事件,大多嫌疑人是来自北非国家的难民,这让默克尔坚决不关边界的政策被置于舆论烈火上炙烤。
在崔洪建看来,默克尔最初没能以复杂视角看待难民问题,“她对德国和欧洲难民接纳能力有着过高的乐观估计,而做出承诺本身则会鼓励更多难民涌向欧洲”。
“单纯接纳难民并不能解决难民问题,这是德国在难民危机中得到的重要教训。”崔洪建说,“所以后来她又提出针对非洲的发展计划,通过促进当地和平稳定和发展消除难民问题的根源,而非被动接收难民。”
感受到民意反弹后,默克尔虽然依旧寻求“欧洲解决方案”,但也务实地收紧难民庇护政策,与土耳其达成协议,阻止难民经土耳其无序入境欧洲。在2016年12月基民盟的党代会上,默克尔坦言,2015年夏天的情况“不能也不应该重演”。
◆难民在欧洲国家避难申请数量
可欧洲边境线开放的那一刻起,无论结局好坏,注定无法逆转。
站在当下,依然难对难民在德国的融入情况盖棺定论。该群体中有不少人找到工作、按时纳税,还有些人申请上了大学。有些地区因移民到来补充了劳动力,但也有许多难民连语言与职业培训都拒绝完成。
总体而言,移民就业率依然远低于德国平均水平。德国劳动市场与就业研究所去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国移民的就业率不到一半,当就业形势刚有好转时,疫情又使许多人再度失业。
难民与犯罪问题的关联性也始终是舆论热点。德国联邦刑侦局《移民背景下的犯罪状况报告》显示,难民群体在谋杀、过失杀人、严重身体伤害和强奸案中的犯罪比例突出。截至2017年年底,该群体约占德国总人口的2%,却在8.5%的犯罪事件中成为嫌疑人。
不过,在犯罪研究专家看来,过高的犯罪率与种族无关,而缘自难民群体中年轻男性比例过高,而无论在世界何处,年轻男性都是犯罪的“主力群体”。
但原因不重要,对难民尤其是穆斯林群体的恐惧依然飘荡在整个欧洲大陆。越来越多本土民众抗拒外来者,也不满于政治精英的决策——在他们看来,政府不该将社会财富施予本不属于这个社会的外来群体。
人心动摇趁势埋下危险的种子,滋养了一波民粹思潮,给德国“另类选择党”这类极右翼政党留下崛起空间。这一党派在前东德地区有着更热情的拥趸者,尽管这些地区并未大量接收难民,也没有为此付出多少财政代价。
另类选择党的政治策略和特朗普如出一辙,那就是区分“我们”和“他们”,该党认为一国资源、机会、财富当然应该优先分配给土生土长的本国人,而不是和“我们”肤色、文化、信仰等等迥异的“他们”。
通过渲染排外情绪和难民威胁,另类选择党在2015年10月的支持率首次超过5%,升至7%,同期默克尔的支持率下降了9%。对于难民危机的政治化利用帮助这个边缘小党打入16个州的州议会,并在2017年的大选中获得了12.6%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这是二战以来首次有极右翼政党进入德国议会。
极右翼扩张意味着联盟政府的败退,主流政党在德国议会的话语权不断被削弱,在地方选举中渐显颓势。崔洪建向“全球报姐”指出,如果没有难民问题,很难想象另类选择党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关于难民的争议性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德国现在的政治格局,客观上也导致默克尔在声望较高的情况下做出隐退的决定”。
对默克尔及联盟党来说,不仅遭遇小党壮大带来的政治碎片化,执政联盟内部也因难民问题出现裂隙——基民盟多年来的姐妹党基社盟(CSU)极力反对该政策,基社盟前主席泽霍费尔直言,默克尔的决定是个“错误”。
为了挽回流向极右翼的选民,多位基社盟领导人选择了更为强硬的排外姿态,例如称“移民是一切麻烦之母”,甚至威胁让默克尔退出执政联盟。然而,这些带有民粹色彩的策略却适得其反,将原本支持多元化的选民拱手送给欢迎难民的绿党。
难民危机也再次考验德国与欧洲的关系。何彼得向“全球报姐”指出,即使就难民问题讨论了6年,欧盟也没能达成共识,大多数国家依然不想接收难民。
如果当初德国登高一呼,其他欧洲国家积极响应,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或许可以成功。然而,中东欧国家普遍不满默克尔强行摊派难民的方案,德国被指责推行“道义帝国主义”——自己享受难民带来的人口红利,却让别国付出不相称的成本。
更严峻的问题在于,政治碎片化不仅困扰德国,也导致了极左与极右党派在欧洲的兴起。欧洲一体化本该淡化民族国家间的疆界,分裂却成为这个共同体的新主题,英国脱欧正是这种分裂最真实的佐证。
德国乃至欧洲再无默克尔
对于主导德国政坛16年的基民盟而言,当小党纷纷崛起,其大党地位被逐步蚕食,政治碎片化消解着默克尔多年来打造的中间道路遗产。
在上一次选举中颓势尽显的联盟党,今年支持率持续下滑,从此前的40%退守至30%,到9月上旬连20%都难维系。直至9月21日的最新民调中,联盟党的支持率勉强回升至22%,但仍低于社民党(25%)。“大党不大、小党不弱”的局面使得本次大选变得难以预测,要获得超过50%的选票以组阁,三党联合将是大概率事件。
这意味着,新政府很可能以右翼联盟党或是左翼社民党为核心进行组阁,左右共治局面再难出现。而在未来,德国政治也将继续面临不确定性。
崔洪建指出,德国政治很难回到以前的道路,因其政治议程相对简单的时代已经过去。“如果德国未来想要回到相对稳定、形成中间共识的状态,要看两种力量的博弈状况——主流政党能否有效稳住地盘并吸收小党的主张以避免政策受到更多挑战;小党在进入主流后能否获得更多执政经验和更全面的执政视野,并改造其相对激进的政策主张。”
德国政治蕴含的变化只会让默克尔难以安心卸任,基民盟的统治能否延续将是首先要接受的挑战。联盟党民调一路走低,部分缘于选民被政治主张更鲜明的小党拉拢,亦有分析指出,默克尔接班人拉舍特的个人吸引力实在有限。
作为基民盟新任党主席的拉舍特同样主张社会融合、愿意妥协和维持平衡,但选民并不买账。他在今年水灾视察现场的嬉笑状态更是引发众怒,遭到媒体痛批。为了力保拉舍特接任,默克尔甚至喊话选民,希望他们在大选中支持自己的继任者,并就左翼政府可能带来的危险发出警告。
大选前夕,拉舍特的受欢迎程度远低于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8月30日,拉舍特、肖尔茨以及绿党总理候选人贝尔伯克进行了三人辩论对决,当晚Forsa进行了闪电调查,36%的人认为肖尔茨表现最佳,拉舍特以25%排在最末;而在“最信任谁”这个问题上,47%的人最信任肖尔茨,仅有24%的人信任拉舍特。
拉舍特在联盟党内部也不受欢迎,70%的联盟党支持者认为应在选前换将,由基社盟主席索德尔取代拉舍特担任总理候选人。
无论谁成为德国新总理,绝无可能拥有默克尔在西方世界的声望,也很难再有后来者可以积累起如此雄厚的政治资本,维系16年相对平稳的治理,进而影响欧洲乃至世界。
默克尔不喜欢“自由世界领袖”这个称呼,但无论如何务实与妥协,或是让政策看起来自相矛盾,她的执政内核始终没有远离对自由的追求,附着其上的则是责任与包容。默克尔所期待和捍卫的全球化,正被这个单边主义与民族主义盛行的时代冷落,但一个自由包容、不互相征伐指责的团结世界,永远是可欲的。
尽管此次大选之后,默克尔不再担任总理,但距离她真正谢幕还有一段时间。在完成组阁谈判之前,本届政府会继续运作,左翼党党团主席巴尔奇(Dietmar Bartsch)预测:“到圣诞节,默克尔仍将是总理。”
如若成真,默克尔将成为二战后德国在任最久的总理。前总理科尔于1998年卸任时,共执政5869天,倘若默克尔执政至今年12月17日,她将超越科尔创下新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