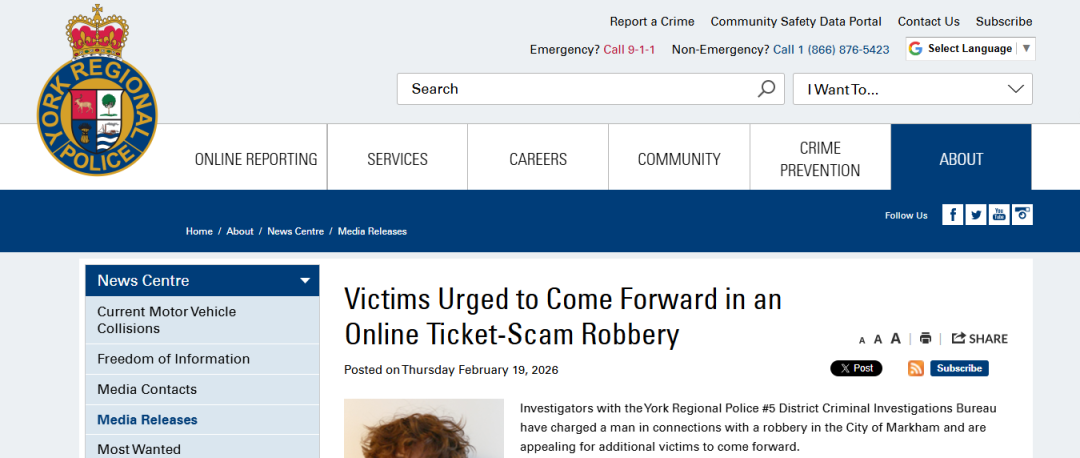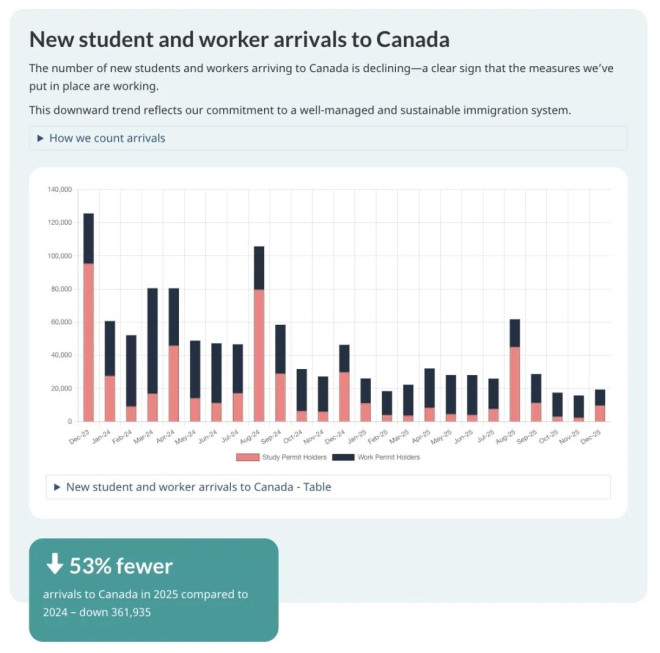谭主了解到,这次会议,是在去年11月双方牵头人旧金山会晤达成的三点重要共识的基础上进行交流的,谈得不错。
站在共识的基础上继续谈,中美的这次沟通,会给外界传递怎样的信号?

这次会议中,中美双方谈到了两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
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要放在全球的大环境下去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同时提高了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预期,给全球经济注入了一些积极因素和稳定性。
而在这样的形势下,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并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
去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在谈到经济时,两国元首达成的一项重要共识,就是共同推进互利合作。
不“脱钩”,也是中美经济领域沟通的前提。
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农产品出口市场、38个州前三大出口市场,据统计,对华出口为美创造了100多万个工作岗位。7万多家美企在华投资兴业,年利润达500亿美元。
正是有着这样的前提,中美经济领域的沟通,才格外有意义。
中美不寻求经济“脱钩”,保持正常的经济贸易投资联系,不仅对两国经济,对全球经济也都是利好因素。
在讨论两国经济形势时,还有个背景值得注意——美国将要走出加息周期。
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经验表明,从两项指标来看,一旦美国的通胀率高于4%,失业率低于5%,美国经济在历史上出现过陷入衰退的情形。
如果梳理美国1965年以来,美联储经历了11轮加息后的情形,只有三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在这个关键当口,美国经济仍然面临“软着陆”的可能性问题。
这样的情形下,美国代表团来到中国,跟中国面对面谈,无论是从国内而言还是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需要跟中国对对表,充分沟通好相关情况,向外界传递更多确定性。

沟通频率,是观察中美经济领域互动的重要视角。
去年9月,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此后,在去年10月、11月,中美经济工作组接连举行两次会议,这一次是第三次。
几乎一到两月就沟通一次,这样频密的沟通,意味着什么?
谭主对比新闻稿发现,相较于去年10月的第一次会议,这一次的经济工作组会议提到的议题更加具体。
会议中,中方直接点明,就美对华加征关税、双向投资限制、制裁打压中方企业等表达了关切。
这是落实双方牵头人共识的切实行动——双方牵头人达成的三项共识之一,就是同意加强沟通,寻求共识,管控分歧,避免误解意外导致摩擦升级。
这几次会谈,中美双方聊的议题很多,中方明确表达对美对华双向投资限制、制裁打压中国企业、对华出口管制、对华加征关税等关切,要求美方切实以行动予以回应。
这样梳理下来,可以看到中美经济领域的互动——先由牵头人在核心关切上充分对表后,双方工作层可以在具体问题上进行充分交流。
与之相对应的,相比于第一次,这一次会议的新闻稿中多出了一个词——务实。
这也说明,中美经济工作组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
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卢锋告诉谭主,中美经贸层保持沟通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果。中美经贸关系当前处在的阶段是,双方在大的认识上总体形成共识,正在进入一个比较常态性的、相对稳定的沟通发展的轨道。
所以,当前,中美经贸层在做的,是坐下来,不断就双方存在的问题和分歧进行沟通。
就拿美对华加征关税来说,中美上一次谈这个问题,还是在去年11月。为何此时再谈,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就在会谈前几天,一份由多个国家的经济学家共同完成的报告显示,美国前总统对华加征关税,在经济上遭遇了失败。
报告中提到,前总统号称对华加征关税能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能为美国带来就业机会,但事实是,这些“政治口号”都没有实现。
第二个细节是,会谈前,外媒报道称,由于美国的原因,“印太经济框架”谈判陷入僵局,在贸易领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而美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初衷,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
这两个细节充分说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并不得法。
谭主也注意到,前不久,拜登政府称正在考虑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和关键矿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在当下这个节点,中方再提对华加征关税问题,也是在提醒拜登政府,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谭主也了解到,接下来,双方沟通将更加深入、密切。

中美经济领域保持频密沟通,不仅有助于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同样还有助于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此前,中美双方牵头人还达成了一道努力应对共同挑战的共识。这一共识,在此次会议中,同样有所体现。
这次美方代表团的牵头人,是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杰伊·尚博。
根据美国财政部官网介绍,杰伊·尚博的职责是帮助财政部制定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汇率问题、气候政策和国际金融监管相关的国际经济政策。
特别是二十国集团,此前,中美两国同时担任过二十国集团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席主席,这些事关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容,都是杰伊·尚博的具体工作范畴。
这次会议,中美双方也专门提到了二十国集团财金合作以及发展中国家债务。
谈论这两个问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美国等经济体正进入“三高一低”的新变局当中。
“三高”说的是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
这两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货膨胀保持高位,其中,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98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的预测,2024年,全球通胀率预计将达到5.8%,仍远高于疫情前约3.5%的水平。
面对高通胀,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启加息潮,结果就是让债务水平本来就不低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了更大风险。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存量是2000年的近5倍。因为加息,当前15%的低收入国家处于债务困境,另外有45%的低收入国家和约25%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债务困境的高风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迫在眉睫。其实,早在2020年的G20峰会上,各国就形成了缓解低收入国家债务困境的初步倡议,但发达国家并不积极。
相反,中国则是G20成员国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缓债总额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中最大,为全球性债务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安全缓冲。
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手段,还是发展。
世界银行曾出了一份名为《下降的长期增长前景》的报告,其中提到,2022年到2030年,全球年均潜在GDP增速将下降至2.2%,为30年来最低水平。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双方牵头人说到共同应对的挑战,也包括经济增长。
中美能在这个问题上做些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罗振兴表示,中美两国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要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中美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国内经济搞好。
而对于当前的中美经济关系而言,搞好各自的经济,不仅要考虑自身,也需要考虑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