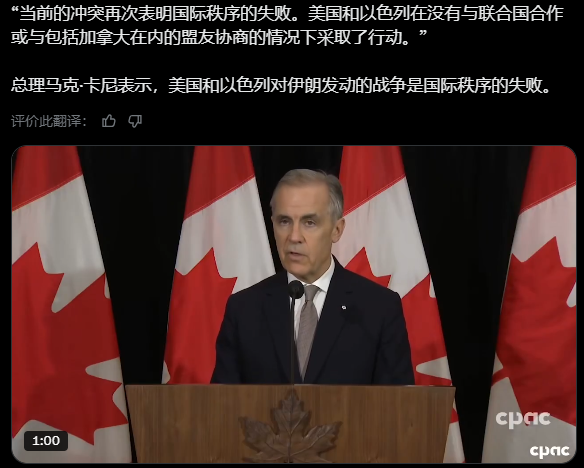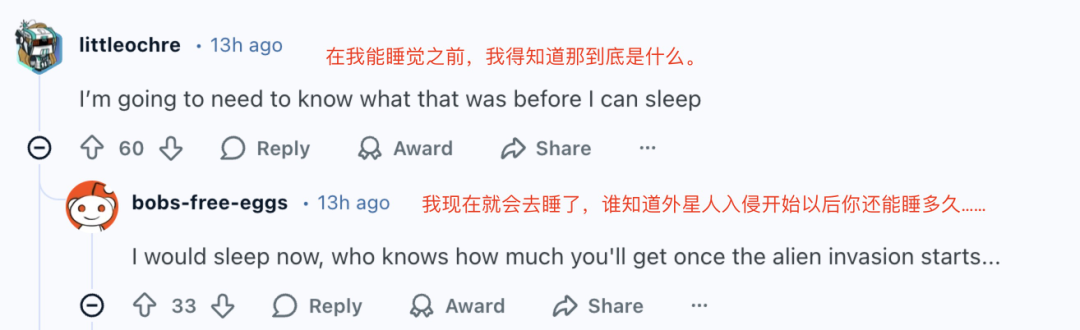选择进山旅游的朋友,除了能感受秋日的凉意,伴随着虫鸣和鸟叫,还能好好亲近一把大自然里的小动物。
猴子也是山里常见的一种动物,聪明灵巧,还会和人互动,时常出没于各大景区。
无论是峨眉山还是黔灵山,猴子都是景区的一块金字招牌。是不是也有朋友,为了一睹“猴哥”的风采,吭哧吭哧地爬到了山顶。
但是,旅游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切记看猴别逗猴。
别看猴子体型小,拦路抢劫,殴打游客,这些景区的恶霸泼猴,可是旅游管理黑名单上的常客。和它们动起手来,人可一点也不沾光。
所以,体型较小的猴子,究竟是如何成为景区一霸的?
景区的猴子,抢东西是认真的
从2015年到2019年,五年间贵州黔灵山公园的猕猴们,已经“故意伤害”及“误伤”游客6700余人[1]。不少贵阳人都与黔灵山的猴子过过几招,其中被猴子打伤严重,甚至住院的也不在少数。
出门旅游,在景区和猴子打了一架,这听起来多少都有些离谱。但是人猴大战,无论输赢如何,都是人猴接触行为的一种。
这正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生命科学学院一项联合研究的重点[2]。以海南南湾猴岛景区为例,当游客与猕猴,在2米内发生威胁、接触、抓、咬以及抢包等互动关系,都会成为这项研究的数据统计对象。
根据2012年到2014年的情况统计,人猴接触的行为按照危险程度,可以分为四种等级类型。
其中,被猴子抓伤以及咬伤,已经是最严重的四级行为。
因为每年在景区被猴子攻击咬伤的游客太多,峨眉山景区甚至贴出了通知,在景区内被猴子围、扑、咬、伤,只要门票包含了意外险,都可以免费打疫苗[3]。
山里的动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猴子,最不让景区的管理员省心呢?
猴子是一种典型的群居动物,像人一样,有着复杂的社交关系[4]。猴群之中,经常因为资源和权力的争夺,大打出手。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地,猴子之间经常会发生斗殴行为[5]。大概是因为打架斗殴在猴群里是家常便饭,所以猴子打起人来,动作也分外娴熟。
此外,猴子的大脑结构与人类相似,都存在一个控制情绪和攻击行为的指令中枢——杏仁核[6]。与此同时,猴脑中的杏仁核尤为发达,加之猴子的雄性荷尔蒙分泌相对旺盛[22-23],所以猴子才表现出了相对较强的攻击性。
猴群在野外的自然状态下,很少与人类接触,所以显得比较胆小怕人,几乎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景区的猴子频繁攻击游客,是由于长期的人工驯化,使得猴子变得不怕人。加上游客没完没了的投喂和逗弄行为,为了争抢食物和自卫,猴子们就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攻击游客。
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了游客增多与猴子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7]。
来自中国计量大学的研究者,通过摄像头网络进行视频监控,收集了南京红山动物园圈养猴群约有90只,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一年的社会冲突数据。数据统计的结果显示,在游客较多的日子,比如周末,猴子的行为更加激进。

许多游客来到峨眉山旅游,是为了一睹猴子的风采。(图/图虫创意)
人猴冲突中,通常人是主要原因[2]。景区的猴子通常是需要靠人工投喂来招引猴群,恰恰是游客的投食行为会增加猴子的攻击行为。这种靠近猴子的喂食行为,会刺激猴子,让猴子觉得游客想要攻击自己,从而触发自卫行为。
发表在《美国灵长类动物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个观点。
研究发现,接受游客投食的台湾猕猴(Macaca cyclopis)的攻击行为,是没有投喂食物猴群的四倍以上[8]。
猴子原本就野性难驯,加之游客图新鲜,又经常在景区招猴逗猴,投喂食物,才使得猴哥们肆无忌惮,成为了景区一霸。
景区的泼猴,都是哪里来的
在世界范围内,观赏和投喂野生猿猴都是最常见的野生动物旅游形式之一[2]。所以,猴子出现在景区,主要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景区开发到了猴群的家门口。
以日本长野县地狱谷的雪猴为例[9],这里在旅游开发前,原本就是野生猴群的栖息地。由于本州岛中部气候寒冷,原本生活在这里的猴子,为了适应低温环境,也学会了泡温泉,便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景观。所以才吸引了大批慕名前来,围观猴子泡汤的游客,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这才有了著名的野猿公苑(SnowMonkey Park)。
另一种常见的原因是,猴群在景区的出现也是旅游开发者为了招揽顾客[10],有意为之,猴子们也是被迫搬家。
近些年频频登上社会新闻的山西历山猕猴源景区,便是被猴子们迫搬家的一个典型事例[11]。
中条山确实是野生猕猴的栖息地不假,但是被开发的猕猴源景区,本不是猴群的栖息地。为了吸引游客,景区雇佣养猴人每天将数百只野生猕猴从山上引到山下的猴场,让游客近距离观赏和喂食。
在国内,四川的泸山景区也是同样的情况[12]。
泸山景区自然状况下是没有野生猕猴群的。1988年,景区兴建之初,为了增加观赏性和趣味性,景区开发者从木里县,引进了101只猕猴在泸山上放养。
泸山地处四川盆地,气候宜人且植被茂密,随着长达数年的繁衍生息,猴群日渐兴旺。2015年时,整个泸山风景区猕猴的数量已经达到六百余只,且分化为数个猴群。
但是,栖息地的改变,也影响了猴子的脾气。
由于大规模的开发活动,景区的自然生态已经无法满足猴群生存和繁衍的条件。
野生猕猴偏爱取食人工投食食物,猕猴食性偏好改变使其适应自然环境能力下降[2]。为了生存必需的食物,原本野生的猴群被迫和游客发生了大规模的接触活动,无需捕猎,只要伸伸手就能得到游客投食的方式,破坏了猴子原本自然习性和当地的生态平衡,除了近亲繁殖带来的物种多样性减少[13],也给生活在景区周遭的居民增添了诸多麻烦。
以历山为例,本来当地居民与猴子的栖息地距离较远,各不打扰。
景区开发后,离景区最近的村庄,饱受猴子之苦。由于景区的大规模开发,猴子原本的栖息地范围被迫缩小,食物的获得变得更加艰难[14]。几乎每隔几周,景区附近的村庄,就会出现一群规模不小的猕猴,饥肠辘辘地到山下寻找食物。
猴子们不仅闯入村民家中偷吃食物,还会在农田里,毁坏庄稼。甚至在村里的河道“随地大小便”,污染水源[11]。
看来,被迫搬家的猴子们,只能把饿肚子的仇,都记到了生活在景区附近的老百姓头上。
那么,对于饱受猴子骚扰的景区居民和游客,就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人猴分离,对人对猴都好
办法不是没有,但是以牙还牙,一定捞不到好处。以猴群的战斗力水平,对人而言,很可能是打输了住院,打赢了坐牢。
根据2021年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猴子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包括峨眉山的藏酋猴、历山和黔灵山的猕猴等)[15],打伤猴子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此外,人对猴子的影响也不小。景区的游客也可能影响猴子的焦虑水平、繁殖率和自然环境适应能力。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和麦吉尔大学的联合研究表明,游客接触下的黑吼猴皮质醇含量高于对照种群[16]。这项研究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持续追踪调查了33只黑吼猴(AlouattaPigra)的350个粪便样本,以记录群体粪便皮质醇水平的变化。这说明,游客的存在与增多,提高了猴群的焦虑水平。
高皮质醇水平,会导致生育力低下和死亡率增加。
在海南南湾保护区,猕猴(Macacamulatta)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后,1985-1989年,游客数量年平均增长率为69.8%,猕猴的年平均繁殖率也由77.8%下降至70.5%[2]。
繁殖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旅游参观人员拥挤逗弄,甚至追打猕猴个体,造成其交配中断,影响交配成功率,甚至导致孕猴流产死产。
与此同时,研究发现黔灵公园的半野生猕猴,更偏爱人工投喂的食物。而游客投喂的食物,基本都是人类的食物,对于猴子而言,往往营养价值过高,容易导致体重超标、引发疾病[17],同时食性偏好的改变,也使得猕猴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下降。
景区使得人和猴被迫相见,导致了种种生态和安全问题。所以,人猴分离,才是正解。
景区人猴分离的主要措施,一般有以下三种[13][18-19]。一是在重要景点设立围栏,防止猴子进入游客区;二是在游客区域加强巡逻,及时处理猴子攻击游客的事件;三是对猴子进行人工喂食,防止猴子进入游客区觅食。
以峨眉山为例,人猴分离取得的效果显著。
景区所采取的“人猴分离”的管理模式,并不是通过防护网去保护人类,或者简单地限制猴群的活动范围。而是通过管理员跟随猴群,主动制止它们和游客的接触,同时也提醒游客不要喂食和挑衅猴群。
截止到2023年,峨眉山景区大约有14个猴群582只猴子,其中清音阁片区有3个猴群约106只,在实行“人猴分离”管理模式后,清音阁猴区猴子抢东西、伤人的情况相比以前大幅度减少[20]。将游客与猴群分开,游客可以远观猴群,同时又有效保护了猴群。
另外,根据印度的猴子治理经验,让猴子来管猴子,也是值得国内景区参考的方式[21]。
新德里的办公大楼搬迁的地区,部分是恒河猴栖息地,为了解决猴患,安保部门找到了比恒河猴体型更大的叶猴来管理恒河猴,猴子的领地意识虽强,但是看到体型比自己强壮的同类,也有所收敛。
所以出门旅游,还是不要在景区招惹猴子,打输住院,打赢坐牢。如果避之不及,路遇恶霸泼猴,还是谨记走为上计。

[1] 贵州省林业局.(2020).科学保护黔灵公园猕猴的建议和意见.
[2] 张鹏,段永江,陈涛&张杰.(2018).海南南湾猴岛景区内猕猴与游客接触行为的研究.兽类学报(03),267-276.
[3] 海峡都市报新闻频道.(2023).游客被峨眉山猴子围扑咬伤,景区回应:买了意外险可免费打疫苗.
[4] Goodfellow, C. K., Whitney, T., Christie, D. M., Sicotte, P.,Wikberg, E. C., & Ting, N. (2019). Divergence in gut microbialcommunities mirrors a social group fission event in ablack‐and‐white colobus monkey (Colobus vellerosus). Americanjournal of primatology, 81(10-11), e22966.
[5] Crofoot, M. C., & Gilby, I. C. (2012). Cheating monkeysundermine group strength in enemy territory. Proceedings of the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2), 501-505.
[6] Amaral, D. G. (2002). The primate amygdala and the neurobiologyof social behavior: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anxiety.Biological psychiatry, 51(1), 11-17.
[7] Xu, A., Liu, C., Wan, Y., Bai, Y., & Li, Z. (2021). Monkeysfight more in polluted air. Scientific reports, 11(1), 654.
[8] Hsu, M. J., Kao, C. C., & Agoramoorthy, G. (2009). Interactionsbetween visitors and Formosan macaques (Macaca cyclopis) atShou‐Shan Nature Park, Taiwan. 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Primatologists, 71(3),214-222.
[9] 苏珊娜·罗塞巴切尔,因格·安德特&南雁.(2004).喜欢泡温泉的日本雪猴. 人与自然(01),38-47.
[10] 郭剑英,熊明均&杨仙.(2019).基于UGC在线点评的峨眉山景区游客满意度研究.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1),53-59.
[11] 红星新闻.(2023).白寺沟猕猴下山.
[12] 环球时报.(2016).泸山本无猴引入酿大灾,景区称治猴患避孕药都试过.
[13]孔小刚,郭卫东,匡三傲,杨倩&路纪琪.(2011).济源五龙口景区猕猴资源现状与可持续利用分析.河南林业科技(04),11-12+15.
[14]Devi, O. S., & Saikia, P. K. (2008). Human-monkey conflict: acase study at Gauhati University Campus, Jalukbari, Kamrup, Assam.Zoos’ Print, 23(2), 15-18.
[1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21).新调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公布.[16]Behie, A. M.,Pavelka, M. S., & Chapman, C. A. (2010). Sources of variation infecal cortisol levels in howler monkeys in Belize. American Journalof Primatolog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Primatologists, 72(7), 600-606.
[17]四川农业大学.(2013).盟员徐怀亮课题组关于藏猕猴研究走进央视科教频道.
[18]沈梦伟,张麒麟&毕孟杰.(2015).我国猕猴的研究综述. 生物技术世界(05),166.
[19]朱源,卢志远,李达,王琦&粟海军.(2019).贵州黔灵山公园半野生猕猴的种群动态.兽类学报(06),630-638. doi:10.16829/j.slxb.150281.
[20]人民资讯.(2023).峨眉山景区推进人猴分离管理,减少猴群伤人事件发生.
[21]澎湃新闻.(2023).为防猴子啃食装饰花,印度新德里G20峰会前安装假猴.
[22]Rose, R. M., Berstein, I. S., & Gordon, T. P. (1975).Consequences of social conflict on plasma testosterone levels inrhesus monkey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37(1), 50-61.
[23]Giammanco, M., Tabacchi, G., Giammanco, S., Di Majo, D., & LaGuardia, M. (2005). Testosterone and aggressiveness. Med Sci Monit,11(4), 136-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