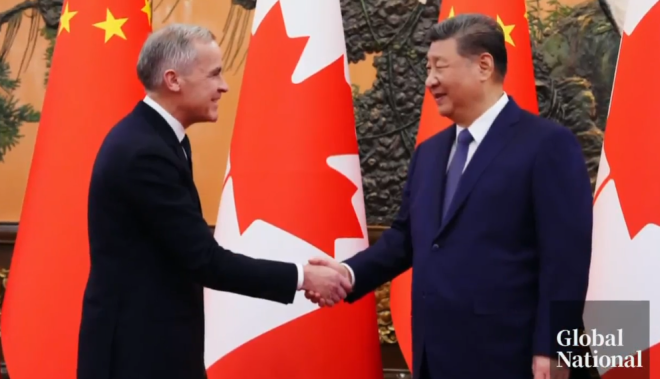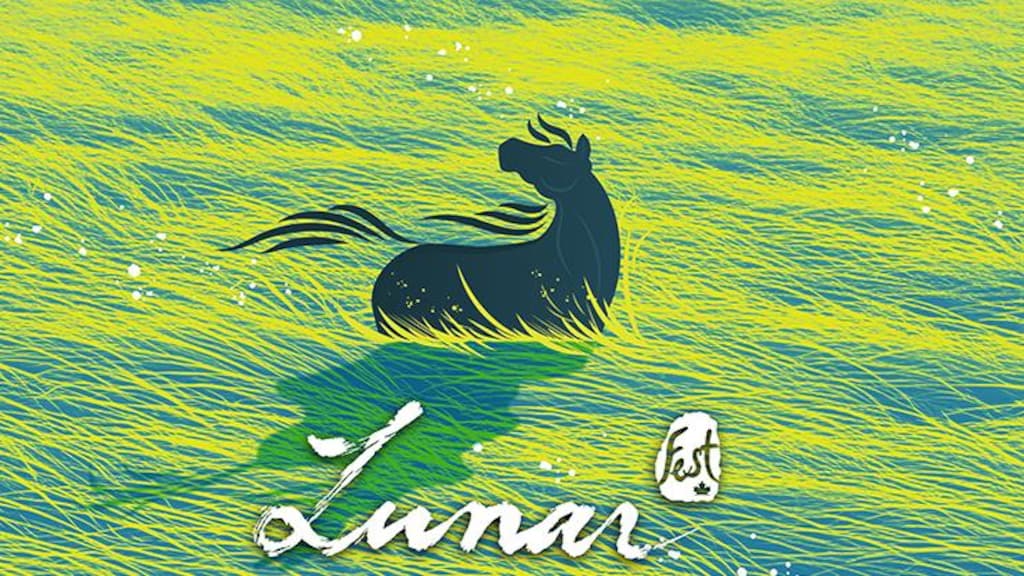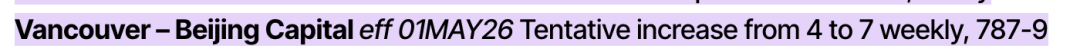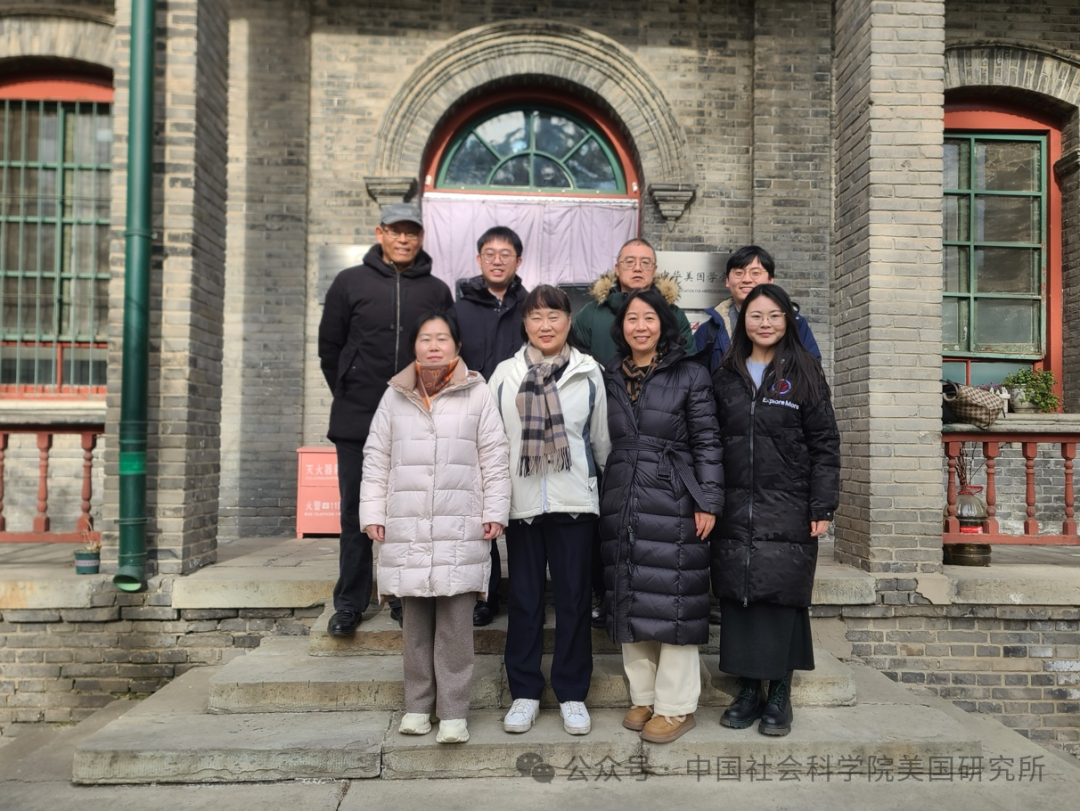痖公记忆真好!那还是前一年加华作协的春假联谊会上,韩牧老引荐我认识痖公,介绍说我帮叶先生整理过录音。痖公说他也有些材料需要人整理。彼时我刚结束了一部翻译稿件,也希望找点有趣的事情来做,又听过痖公几次讲话,知道他的经歷丰富多彩,便主动请缨。
9月19日,首次登门「桥园」寒暄两句后,开始工作。痖公从台静农说起。我记录的方式是笔记加录音。痖公从十点谈到十二点,滔滔不绝。正巧痖公的小女儿小豆在家,提醒我们去吃饭。痖公推荐了周围几家餐厅,因为都是北方人,意见一致地去吃面–越南面。由我开车,我们两个人很快到了越南面馆。痖公遵从西方礼节,拉门、让位、结帐,毫不含煳,令我着实不安。
为了节约时间,我申请以后中午都在痖公家煮饺子。日后形成了我煮饺子、痖公剥蒜的固定组合方式。痖公剥蒜后,要用刀拍碎,放在两只酱碟中,再加上台湾产的「壶底油」。某次壶底油用光了,痖公加了鱼露,味道也很不错。痖公很会买饺子,他搭朋友车买菜时,专门去丽晶广场买手工包的饺子。「我知道哪家包的饺子好吃。」痖公说起来不无得意。
「桥园」和我的住所相隔三十多公里。GPS指示的标准车程是35分钟,我车技不佳,又常遇堵车,一般开过去要一个小时。路上经过三段高速,尤其是最后一段,要上桥,坡度大,小车马力不够,上桥时感觉将油门踩到底也达不到九十公里的限速,颇为吃力。天气不好时,遇到大雨、大雾,更是心惊。上到顶端又是一路下坡,两公里后左转出高速,立即滑入一段小路,路旁是参天大树。每次我转下高速时,都觉得无比轻松,任凭车子一路滑行,我知道,马上要走进痖公五彩缤纷的记忆中了。而工作结束后,开车上路,又是相反的感受。从幽静的社区拐入大路,一路轰鸣着回到红尘。
来去的路有一小段不同。回去时,为了避免上坡堵车时熘车、坡起,喜欢走菲沙河旁的一段隧道。那段路被誉为大温地区首堵。堵车时,一般都不用踩油门,靠着踩、松剎车熘车就够前进了。我倒不介意堵车,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放松大脑,回味听来的故事。某个冬日,河边大雾,雾气遮蔽了周围的车辆、景致,一时觉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觉世事苍茫,彷彿驶在民初的石板路上,眼前出现呢帽长衫者都不会惊奇。大雾停滞在主路前–我也在併入主路后清醒。而先前那几分钟的空灵感受像一滴露珠般凝固在记忆中。
写作的方式是我们当面录音,我再录音整理。听录音,有很多趣味。正在谈诗歌写作,会听到我说「您的猫可能要进来」–那是小豆的爱猫遛早回来了,等在书房通往后院的门外。它很安静,每次想进来时,就在外面默默地等待。于是痖公停下述说,去给猫开门。或者是「噹、噹、噹」的敲门声,然后是痖公的脚步声、开门声,以及和门外的人用英语道安的声音–这往往是邮差或送午餐的。痖公的大女儿小米常年给痖公订购营养午餐,送到家。我来时,也一起分享营养午餐;有一次还遇到附近的孩子挨家兜售自做的蓝莓酱,痖公毫不犹豫地买了一瓶。
痖公的回忆录是个人口述史,写自己的私事,写世俗风情、文坛故旧,也写时政秘闻,颇似古代的笔记小说。读博做研究时,我从各朝代笔记小说中获益不少,非常清楚它们的价值。个人口述史往往弥补正史之不足,尤其能够解释彼时司空见惯而后代摸不着头脑的那些「边角小事」,还时而有些勾陈揭秘。比如吸鸦片,他说那时是时尚,中产家庭来了客人,不招待鸦片都不好意思;比如闻一多遇刺,原来和歷史课本教的不一样。
受过戏剧演出的科班训练,又担纲过《国父传》那样的大戏(一年内曾演了七十多场),痖公很会讲故事。说到南阳的集市时,痖公笑眯眯地闭起眼睛说:「我现在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当时的情景–满街都是人,街上卖糖葫芦的、卖其他东西的,车马喧腾,真像是到了波斯市场。」跟着我就接口说:「真想进到您的眼睛里也去看一看。」是真的想。痖公的笑容、微微颤动地合着的眼皮,午后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白头髮上,那一瞬间让我想马上跌入到痖公的记忆里以身临其境,像哈利·波特跌入冥想盆一样。
每次录音后,我大约要花几天到一周的时间将录音整理成文字、形成段落,积攒多了,编辑成文章。一篇大致成形后痖公通读校改,反覆修订。痖公改稿子改得很细,一页稿子改得「通篇红」比较常见。他写繁体,竖行,比横行简体书写佔地方,页边空间不够时,痖公会根据需要粘贴不同宽度的「白纸」。「白纸」是废文稿的背面,有时候一页纸几片粘着的边角料取自不同的文稿,白度不同的贴边为稿件蒙上了淡淡的歷史感,让我觉得这些字是穿行了很久很久才走到现在,走到这里的。
从南阳到台湾再到加拿大,痖公的一生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我能做的是尽量多地帮他捡拾一路散落的时光碎片。如今,这些缤纷的碎片缝缀起来,便成了已出版的《痖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