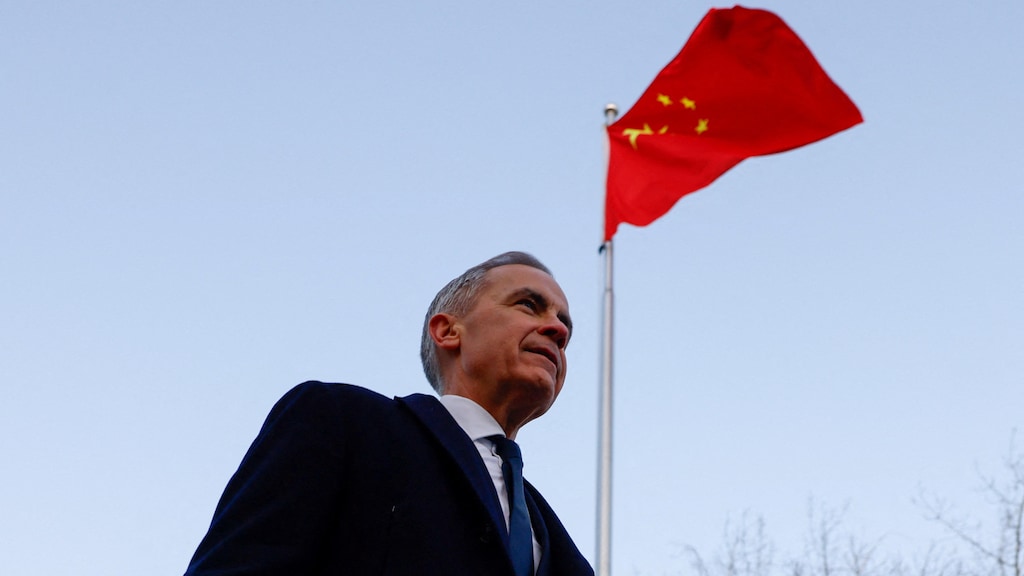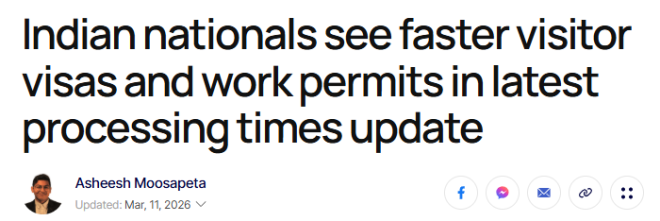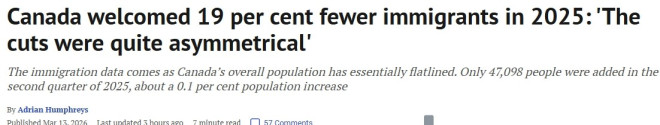勃兰登堡门位于东西向贯穿柏林的轴线中点。有一天,我一路沿着菩提树下大街从马克思-恩格斯广场漫步至此,天色已近黄昏,火红的云霞映衬着金色的勃兰登堡门,仿佛回到1933年那个夜晚,纳粹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希特勒成为了德国的总理,柏林人在希特勒最忠诚的支持者——约瑟夫·戈培尔盛赞“一个完整民族崛起”的激情演讲中,纷纷走上街道。他们载歌载舞,手持火把穿过勃兰登堡门,并最终将这片火焰投向整个欧洲。
靠近勃兰登堡门南面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诉说着这段历史充满悲伤的一面。根据文件记载,1933年欧洲的犹太人人口超过900万,大多生活在“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或影响的国家。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近三分之二的欧洲犹太人遭到了迫害。
2711块高低起伏的混凝土石碑,形似2711座大小不一的石棺,构成了占地1.9万平方米的广阔“公墓”,即便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也散发着冰冷肃穆的气息。嬉戏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进入其中,又在迷宫似的走廊穿梭过程中回归沉静、庄重。碑林下面的档案展览馆,补充了大屠杀中许多犹太受害者的名字,这些名字伴随着一段段简短的传记,被安放在一间房间内。
不过,由于从1943年开始,战争形势越来越严峻,德国和轴心国同盟摧毁了大部分现有的文件,其中包括死去的犹太人的物证。更多的姓名,被遗忘在历史中。犹太教典籍《塔木德》中写道:“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忘却时,这个人才算真正被遗忘。”这句话也正好诠释了“二战”电影《波斯语课》所讲述的故事核心。
“汤匙”是“bala”,“猪肉”是“tsvajn”,“肉”是“gunk”……在位于法国的集中营里,比利时犹太人吉尔斯不得不全神贯注地记着这些不存在的词,因为任何失误都意味着死亡。吉尔斯本来应该已经死了,就像其他同行者一样,在森林里被枪毙,但他用面包交换来的波斯语书救了自己一命。他谎称自己是波斯人,而非犹太人,于是吉尔斯被带到了集中营的指挥官克劳斯·科赫面前。
纳粹科赫虽有军衔,但实际上只是一个掌管后勤的大厨。他计划战后在德黑兰开一家德国餐馆,一直想学波斯语。吉尔斯的法语和德语都说得很好,对波斯语却一窍不通,然而为了生存,他必须成为科赫的波斯语老师。
起初,科赫并没有全然相信他的身份,他清楚地向吉尔斯表明,如果吉尔斯背叛自己的信任,就会亲手杀了他。在这场没有回头路的危险游戏中,欺骗和谎言成为吉尔斯“活下去”的武器。他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够把一门不存在的语言,持续不断地教给这个随时可能杀死自己的男人。
 每日的波斯语课,都是吉尔斯和科赫有关未来的希望
每日的波斯语课,都是吉尔斯和科赫有关未来的希望
“邪恶不是与生俱来的。”佩雷尔曼说,“它源于一系列选择,一开始有些选择相当少。”如同犹太裔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包括科赫在内的许多纳粹士兵,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只是普通人,却在集体主义的体制内被同化,进行着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佩雷尔曼认为,展现这些德国纳粹士兵的人性,表现他们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而非将他们符号化,视为邪恶的象征,是对纳粹行为更有力的控诉。
怀着这种审视的目光,《波斯语课》避免了对集中营生活的悲惨描述,也不满足于把纳粹简单地描绘成杀人犯。相反,佩雷尔曼详细地描写了纳粹党员们在集中营的日常生活。男女党卫军士兵间的爱情,上下级军官的政治斗争,办公室里的闲言闲语,舞会前夕的争风吃醋,还有那难以忘记的愉快野餐。伴着手风琴愉快的节奏,一切都让人联想到现代社会的工作日常。在佩雷尔曼看来,尽管这是发生在“二战”时期的故事,却在当下分裂的政治环境中充满警示作用,“这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
德国演员拉斯·艾丁格对科赫这个角色充满层次的演绎,令观众们在故事的结尾对这位纳粹军官生出巨大的同情。他将莫大的信任给予这个假冒的波斯人,甚至在最后给了吉尔斯“生”的机会,却遭到对方彻底的背叛。影片中科赫有无数次机会识破吉尔斯的伎俩,只要他愿意认真对那本写满犹太囚犯的姓名簿稍加审视,然而,始终未曾尊重过这些不断消逝的生命的科赫,只是漠然地把这些姓名视为随时可以划去的一行行字符。
电影最后,吉尔斯默默背诵出了2840个名字,这是他日复一日背诵的2840个假波斯语单词,也是2840个逝去的犹太同胞的生命。它们帮他活了下来,却没能有机会跟他一起活下去。
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受难者的名字被遗忘。“二战”前的柏林,是世界上居住着最多犹太人的城市之一。当希特勒——这个在慕尼黑出生的奥地利人——将“占据”柏林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后,柏林便在欧洲身负重孽,血债累累,但它并没有选择忘却自己的错误。
1945年5月,如果你站在勃兰登堡门周围的废墟中,可能会想,柏林再也不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欧洲首都了。在战争结束的前两年,柏林有1.5万多栋大楼被英美的炮弹炸毁。在最后两周的决战中,苏联红军的数千架飞机盘旋在柏林上空,投下了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和汽油弹。战争结束后,柏林城区几乎变成一片废墟。然而,柏林人谨慎地重建了自己的城市,始终把对被残杀的欧洲犹太人的纪念作为其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
沿着菩提树下大街穿过博物馆岛,在柏林洪堡大学旁的新哨岗便是一处见证。新哨岗始建于1818年,最初是用于庆祝国家军事的胜利,冷战时期属于东德。当1989年德国统一后,新哨岗内放入了一座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雕塑作品《母亲与亡子》,它才有了今天的纪念用途。从屋顶圆形天窗中倾泻而下的日光,洒在这名怀抱死去孩子的女性身上,她的悲恸令人将注意力从军事记忆转移到所有战争的受害者身上。每日在雕像前摆放的鲜花,表明那些逝去的生命未曾被人遗忘。
然而,在《波斯语课》电影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演艾丁格批评了一个事实:如今在德国,人们有时会说大屠杀是过去的事情,“我们是无罪的,我们是新一代”。但是,当他想到祖父曾参与过战争,父亲则诞生于战争时期,他仍然认为,“直到今天,作为一名德国人,我仍然深受创伤”。
事实上,每个有良知的德国人都无法逃避内心的责罚,这也令地处德国北部的柏林更添凄苦萧瑟。毕竟,当纳粹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附近设立拷问站,当他们先是禁止犹太人购买鸡蛋,随后又禁止犹太人购买书籍时,当各色商铺为犹太人关上了大门时,大部分德国人仍旧悠闲自在地享用咖啡与蛋糕,漠视现实中发生的一切,眼睁睁地看着犹太人被运往集中营。而纳粹政府数量庞大的建筑投资项目,确实使数十万德国人从中受惠,看似日益稳定与富足的生活,令德国境内反抗的声音日益削弱下去。
德国人选择重建柏林来铭记自己曾经的自私与冷漠。来到柏林之前,我未曾想过自己可以离“二战”的历史如此之近。菩提树下大街毁于“二战”,现在的街道是战后按照原貌重建的,道路两侧多为大体量、公共性的新古典主义纪念建筑,而不远处的德国国会大厦、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恐怖地形图、查理检查哨、柏林墙,哪个单独拿出来说不是一段赫赫有名的历史?
“巴黎永远是巴黎,但柏林从来都不是柏林。”法国前文化部长杰克·朗敏锐地捕捉到了柏林独特的气质。柏林在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故事与大多数城市的历史截然不同。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以来,变化是这座城市里唯一不变的东西。今天的柏林,仍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融合了历史与文化的变迁,新的想法令旧的空间得到了复兴和改造。
导演佩雷尔曼用犹太受难者的名字,在影片中为他们建起了一座纪念碑。而柏林将无数欧洲犹太人的姓名嵌入了自己的城市结构当中。或许正是因为德国愿意直面并检讨过去,柏林才得以重新复苏,并成为一个包容、多元的城市。“一位受难者,一块纪念牌”,当我穿过柏林街巷,用手抚摸不时出现在房屋门外人行道上篆刻着的被驱逐出境的犹太居民姓名的铭牌时,柏林离同为“二战”受害者的中国人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