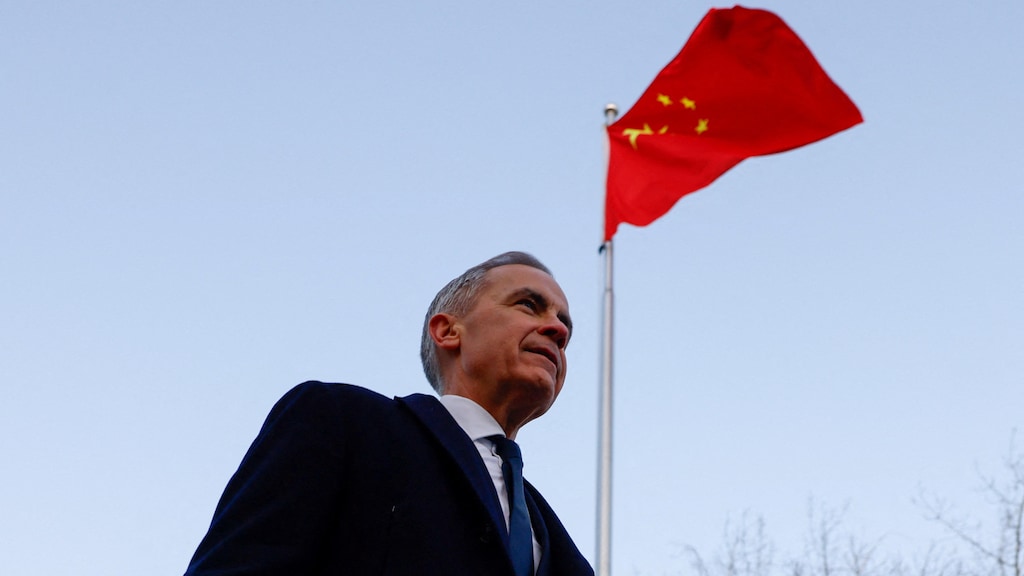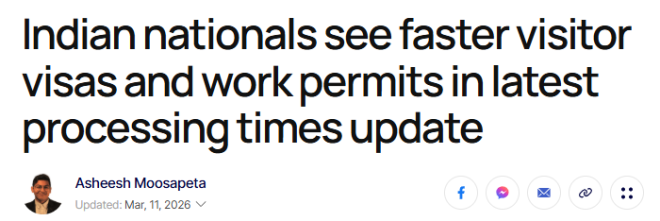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表了一篇Ira Wells的专栏。他在多伦多大学教授大一新生的Vic One特色课程。
文章说,有些国家鼓励竞争,而加拿大人却喜欢垄断。

当然,加拿大有竞争局,这个政府机构声称说要 “为加拿大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促进竞争”。与此同时,加拿大电信三巨头占据90% 的业务:罗渣士(Rogers)、贝尔(Bell)和研科传动(Telus)瓜分;两大航空公司占据了 80% 以上的国内市场份额:加拿大航空公司(Air Canada)和西捷航空公司(WestJet);六大银行控制了80%的财富;食品杂货行业50%以上的市场份额由 Loblaws 和 Sobeys 控制。各行各业都处于近乎垄断的状态。
加拿大只有一支NBA猛龙蓝球队和一支MLB蓝鸟棒球队并不违和,就像只有LCBO在加拿大最大的省份卖酒一样,是没有异议的。
加拿大对垄断的钟爱有多种原因,从我们的历史和地理位置,到同情商界巨头的统治阶级。然而,在这些因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关于加拿大起源的故事。这个被著名教授弗莱(Northrop Frye)称为 “堡垒心理”(garrison mentality),即加拿大在建国前长期受到英、法两国的殖民统治,在建国后又遭受邻国美国的强大冲击,垄断成为加拿大人生存下去的法宝。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坚信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竞争并不总是对每个行业都有意义。从历史上看,政府一直援引”公共运输”(common carriage)原则来监管那些其服务对公民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行业。根据学者蒂彻特(Zephyr Teachout )的说法,从镀金时代(Gilded Age)开始,政治家和企业家就将对社会非常重要,但需要集中供应的商品和服务,如水、电、煤气、电报和公交垄断,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公用事业”。
然而,加拿大人对垄断和近似垄断的接受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公用事业。我们对垄断极其热爱,甚至愿意这些最大的公司继续肆无忌惮地扩张而买单。
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2022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加拿大的手机资费是世界上第二昂贵的,比澳大利亚贵七倍,比法国和爱尔兰贵 25 倍,比芬兰贵1000倍。另一项研究发现,从加拿大出发的国际航班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加航(Air Canada)和西捷(WestJet)的国际航班为每100公里行程平均价格为123.52元,而越洋航空(Air Transat)相同距离的价格为 57.02元。加拿大人的支票账户平均服务费为 11元,而美国该账户平均服务费为 7元。加拿大的牛奶比美国贵 25%,至少部分原因是我们的乳制品垄断。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在美国南部,从温和的民主党人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到共和党人霍利(Josh Hawley),各政治派别的政客们都打着反垄断的旗号。很少有人像沃伦(Elizabeth Warren)那样凶猛,她经常抨击大科技公司、大制药公司和其他企业集团。
沃伦在2017年警告说:”当这些巨头扼杀竞争时,物价就会上涨,质量就会下降,工作机会就会被淘汰。大规模合并意味着大公司可以将较小、较新的竞争对手拒之门外。这意味着大公司可以压制创新,可以压制他们不喜欢的想法和声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拿大的政客们无论站在哪一边,都与我们自己的企业家们相处融洽。加拿大缺乏强大的反垄断运动,也许是因为我们最大的公司都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更隐蔽的是,我们不为人知的民族神话让我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加拿大企业不管其是否是最贪婪、最粗劣的企业,也必须受到保护,因为我们必须互相拯救。
这些说法不仅灌输了一种加拿大人无法参与竞争的观念,而且还灌输了一种竞争观念本身就不属于加拿大的观念。这种说法让极少数、主要是同种族的企业精英获益,对加拿大消费者、工薪阶层和有色人种造成了巨大损害。
加拿大的这段垄断历史与英国在北美的殖民主义遗产密切相关。1670 年,英王查尔斯二世向”哈德逊湾公司”颁发了皇家为委任状,建立了商业毛皮贸易垄断地位,并在加拿大西北划出一片土地,相当于地球陆地面积的十二分之一。
这块地后来被命名为鲁珀特领地(Rupert’s Land),是以查尔斯国王的嫡亲堂兄、HBC 的首任总裁鲁珀特王子的名字命名的。哈德逊湾公司(简称 HBC)不仅获得了商业垄断权,还获得了对该地的控制权。商人的到来不仅为HBC公司开辟了贸易路线,还扩大了其商品的种类。该公司将军事控制与企业管理相结合,积极购买土地,制定贸易政策,经营各个领域。在公司盛期,占领了整个北美洲的毛皮市场。但是,在19世纪中叶,随着贸易方式的变化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毛皮市场的需求下降,公司的销售额也开始下滑。在19世纪末期,加拿大西北公司与荷兰西印度公司合并,公司的管理权逐渐移交给加拿大政府。
随着加拿大工业在 19 世纪的发展,垄断仍然是家常便饭。学者雷诺兹(Lloyd Reynolds)在 1940 年出版的《加拿大的竞争控制》一书中指出,加拿大最早的商业 “似乎主要是在家庭之外进行的,主要掌握在当地的垄断者手中。乡村磨坊、乡村铁匠铺和乡村马具制造商受到运输限制的保护,免受外部生产商和其他地方的竞争”。
铁路本身是垄断行业,它的到来带来了一些竞争,同时也带来了遏制和压制竞争的强烈愿望。雷诺兹认为,对 19 世纪加拿大商业的早期调查”揭示了已经存在的全面垄断利益联盟(cartel)”。
这种垄断趋势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加拿大的国内消费市场相对较小,而加拿大幅员辽阔,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有些人认为,这种情况使得垄断在加拿大市场不可避免。雷诺兹发现,多年来帝国石油公司(Imperial Oil)几乎提炼了加拿大所有的石油。
还有人认为,加拿大的垄断者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发展壮大,是因为他们的剥削不像他们的美国邻居那样明目张胆。经济学家威尔逊(George Wilson)指出:”我们从来没有洛克菲勒、古尔德和他们的公司那样公然滥用经济权力。因此,在加拿大,对巨头或垄断势力的不信任感并不像在美国那样普遍。”
尽管加拿大有旨在遏制反不正当竞争商业行为的法律,但威尔逊发现,长期以来,这些法律的执行”被动而无效”,这是因为作为立法机构的议会长期被商业思维所左右。威尔逊提到了前贸易和商业部长史蒂文斯(Henry Herbert Stevens),后者诋毁了 1923 年的《联合调查法》: “我对该法案的主要批评是,它实际上将是普通的、合理的商业意识宣布为犯罪。
尽管《联合调查法》旨在防止兼并和反不正当竞争的商业行为,但渥太华的一些政客却认为,这种行为是完全合理的,甚至是更可取的经营方式。
尽管渥太华政府不断试图纠正这种做法,比如在2022 年,政府通过了《竞争法》修正案,禁止雇主们之间达成固定工资和禁止挖墙角的协议,但历届政府都未能有效抵制垄断倾向。今年春天,工业部长商鹏飞(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批准了罗渣士公司(Rogers)斥资 260 亿元收购Shaw电信公司的交易,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本已集中的电信领域的主导地位。包括商鹏飞在内的该交易的支持者认为,尽管减少了阿尔伯塔省和卑诗省消费者的选择,但该交易可以”推动加拿大全国的手机资费下降”。(详情请阅读:渥太华同意罗渣士收购Shaw后,加拿大人的手机费会下降吗?会大裁员吗?)
所有关于加拿大对垄断的钟爱的解释最终都指向我们对过去的神话。弗莱教授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文化想象力通常将大自然视为再生或更新的场所,想想梭罗(Thoreau)的瓦尔登湖或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精神升华,而加拿大的荒野则是 “深深的恐怖”。我们的荒野不是快乐或精神复兴的源泉,而是创伤和无望的源泉。我们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人们在丛林中曝晒而死、被活生生吃掉、坠冰而死、发疯的故事。
与这种可怕的自然景象相对的是维持个体生命的部落。弗莱教授在《丛林花园》一书中写道:”这些孤立无援的社区居民不得不对维系他们的法律和秩序肃然起敬,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巨大的、不假思索的、来势汹汹的可怕环境。这样的封闭部落必然会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堡垒心理(garrison mentality)的东西。”
堡垒心理要求堡垒保护范围内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抵御致命的外来势力。弗莱教授认为,一个人要么是战士,要么是逃兵。这样的条件并不能发展个性,更不用说内部竞争了。堡垒心理的膨胀确实带来了”一种支配性的从众心理,在这种心理下,任何原创性的东西都无法自然生长”。
说白了,弗莱教授对18 世纪堡垒中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恐惧的、不可复制的殖民者心态,这种心态来自于想象自己四面楚歌,求助无门。加拿大人之所以对内部竞争深恶痛绝,是因为我们相信大家可以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共同抵御门外来势汹汹的世界。然而,抵制集体的命令,更不用说联合来自外部世界的对手,就是堡垒的”逃兵”。
“堡垒心理”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传承一个名称,它迫使我们不假思索地服从我们被告知的集体利益。
现在,堡垒的围墙已不再是木制的栅栏,而是社会结构,但我们心中的堡垒仍在继续扩散,大概是为了防止加拿大各行业被外国投资干死。我们的政府批准兼并,支持市场整合,理由是更大的加拿大公司更有可能生存下来。
《多伦多星报》和Postmedia拟议合并案的幕后推手就持有这种论调,他们认为,更大的规模将使更大的实体”能够与全球科技巨头竞争”。现在,虽然这一合并案已被放弃,但支持者们仍在争论合并后加拿大新闻能更有效的得到”保护”。
类似的观点也在农业协会中流传开来,这些行业协会本应保护我们的鸡蛋、鸡肉和乳制品行业,并为消费者保持低廉的价格。从理性上讲,我们知道高消费价格可能是这些行业效率低下的结果,而行业协会无权强制提高效率,因此就像学者雷诺兹几十年前所说的那样,”是现有投资的合法庇护所”。然而,我们对这些事实的理解却被一种民族保护意识所淹没,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一致对外。
事实上,我们无意识的民族意识往往与我们有意识地声称对世界的了解相悖。例如,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加拿大严重的财富不平等(财富最多的1%的家庭拥有总财富的四分之一,而财富最少的40%的家庭拥有仅拥有总财富的1.1%),以及不平等加剧的有害后果,从负面的健康结果到较低的经济增长。然而,我们似乎忽略了罗杰斯(Rogers)家族拥有约100 亿元的财富,同时加拿大消费者的手机资费在世界上也是最高的。
在政治之外,一些保守人士长期以来一直以加强竞争和提高市场效率为诉求来抨击垄断,但进步人士同样应该对垄断趋势将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方式感到愤怒。
虽然加拿大反垄断民间组织确实存在,但加拿大急需一个主流组织来宣传反垄断。这种立场需要勇气。据加拿大竞争局称,在过去的14年中,操纵面包价格的行为已从我们的腰包中榨取了数百万元,谴责这种行为是一回事;而站出来反对那些加强反垄断立法的特殊利益集团和律师则是另一回事。
(相关阅读:加拿大面包商因操纵价格被罚5000万元)
我们还必须正视那些潜在的民族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情绪已经潜移默化到政治学和经济理论中。虽然我们不再受HBC的统治,但我们甘心继续蜷缩在经济堡垒和工业堡垒中,这迎合了我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但却只会将财富重新分配给顶层,并阻碍我们的经济潜力。
堡垒心态催生了加拿大企业固步自封,继续统治着加拿大人的经济生活,这种心态已经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提高竞争力不仅可以通过新的经济政策来培养,还可以通过对加拿大在世界上的更友好、更稳健的地位来培养。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说过:”世界需要更多的加拿大”。我们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吗?为什么不敞开大门一探究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