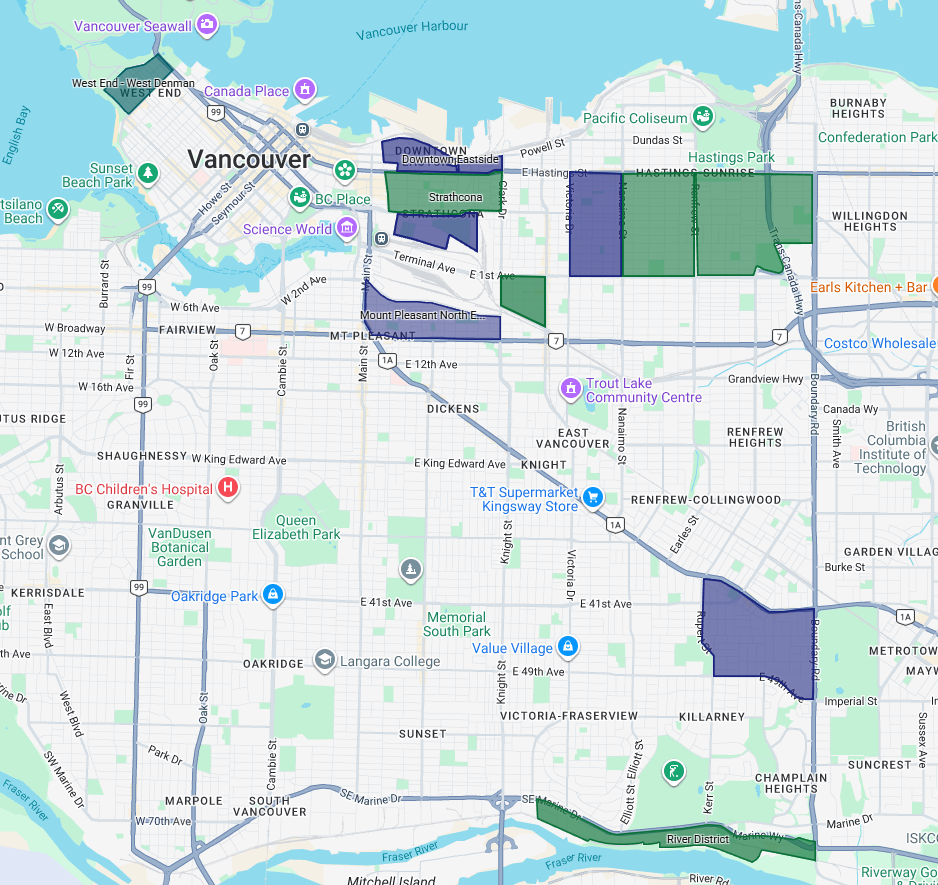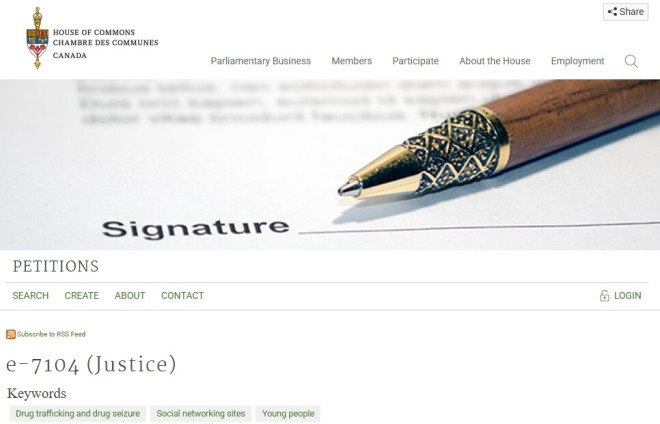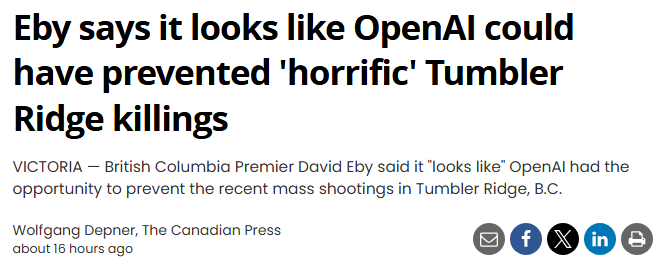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在美国,这是一个悲观的季节——事实上,是一个悲观的时代。
悲观有多种表现形式。进步派悲观主义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头戴“让美国再次伟大”帽子的法西斯主义,或者是新版《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保守派悲观主义认为,从小学到五角大楼,所有的机构都被觉醒革命占据。黑人悲观主义认为,黑人一直被系统性的、无法消除的种族主义排斥在外。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悲观主义认为,这个国家和他们几代人熟知的价值观正被自以为是、中饱私囊、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精英们劫持。
还有中间派的悲观主义:我们正在失去制度能力、文化规范和道德勇气,这些都是在社会的几乎各个层面达成务实妥协所必需的。零和竞争现在成了我们的默认设置。
各种悲观主义可能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但它们都建立在不可否认的现实基础上。2012年,美国大约有4.1万人因吸毒过量死亡。去年,这一数字超过了10万。2012年,每10万人中有4.7人被谋杀。去年,该数字估计达到了约6.9人,增长了47%。十年前,你很少听说劫车的事。现在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入店行窃也是。在疫情之前,美国的心理健康水平就已急剧下降,2007年至2019年期间,青少年重度抑郁发作增加了60%。我们对封锁和学校关闭所造成影响的了解表明,情况已经变得更糟。
经济学也说明了类似的情况。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在2017年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论文章中指出:“21世纪的美国在某种程度上设法为其财富所有者创造了明显更多的财富,同时为工人提供的工作明显减少。”正是由于失去了有意义的工作——劳动带来的骄傲、目标和尊严也随之蒸发,我们才看到中年美国白人的死亡率惊人地上升,通常是因为自杀或滥用药物。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你已经明白了。即使没有日常的迹象让你想到卡特时代的通货膨胀,这感觉也已经很像另一个卡特式的萎靡时代,再加上一个不受欢迎的总统,他往往会激发更多的同情,而不是信心。
那么,为什么在谈到美国时,我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因为当我们充满韧性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却是脆弱易碎的。当我们设法灵活变通的时候,他们却只能保持原状,或是分崩离析。
本周,有两件事有力地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在莫斯科, 普京按惯例发表了5月9日的胜利日演讲,在演讲中,他怀念一个一定程度上经过虚构的过去,只为维持眼前完全是虚构的谎言,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继续一场对他不利的战争。
普京迟钝地发现,羞辱、颠覆和摧毁的力量,远不及魅力、激励和建设的力量——后者几乎是自由国家与生俱来的。克林姆林宫或许还能以强势手段取得某种可以称之为胜利的东西。但它的回报将主要是它所制造的废墟。乌克兰的其他地区将找到繁荣发展的方法,理想的情况是成为北约和欧盟的一员。
与此同时,在上海,超过2500万人仍处于严格封锁下,这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反乌托邦,盘旋的无人机通过扬声器警告居民“控制你灵魂中对自由的渴望”。现在还有人认为,中国对大流行的处理——它的骗局、平庸的疫苗、明显失败的“清零”政策,以及现在这种给最富裕的城市带来饥饿和药物短缺的残酷封城——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吗?
尽管中国在过去45年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进步,但它仍然是一个沉迷于培养夸大幻想的波将金式政权:关于国内和谐(借助庞大的监控系统和监禁营);关于技术创新(借助前所未有的知识产权盗窃);关于不可阻挡的经济增长(借助操纵统计数据)。这种幻想可能会为北京赢得地位。但它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真相的系统性否认,甚至其政权本身也无法得知真相。
相信自己宣传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其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再看看普京,他真的相信自己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这又把我带回美国。就像独裁统治宣传自己的优势却隐藏自己的弱点一样——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己——民主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们沉迷于自己的弱点,甚至忘记自己强大的优势。这是我们悲观主义的根源。但矛盾的是,这也是我们最深刻的力量:拒绝把目光从我们的缺陷上移开,我们不仅承认它们,而且开始修复它们。
我们重新考虑。我们开始适应。在充满弹性的灵活中,我们找到了新的成长方式。
我们在削弱右翼煽动者、驳斥左翼空想家、促进种族公正、扭转犯罪浪潮、重振政治中心和重振美国理想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我们的问题可能很困难,但它们既不是无法解决的,也不是新的。
那些没有我们的自由的人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 Bret L. Stephens自2017年4月起担任《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面的专栏作家。他于2013年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时获普利策评论奖,此前还曾担任《耶路撒冷邮报》主编。欢迎在Facebook上关注他。
- 翻译:晋其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