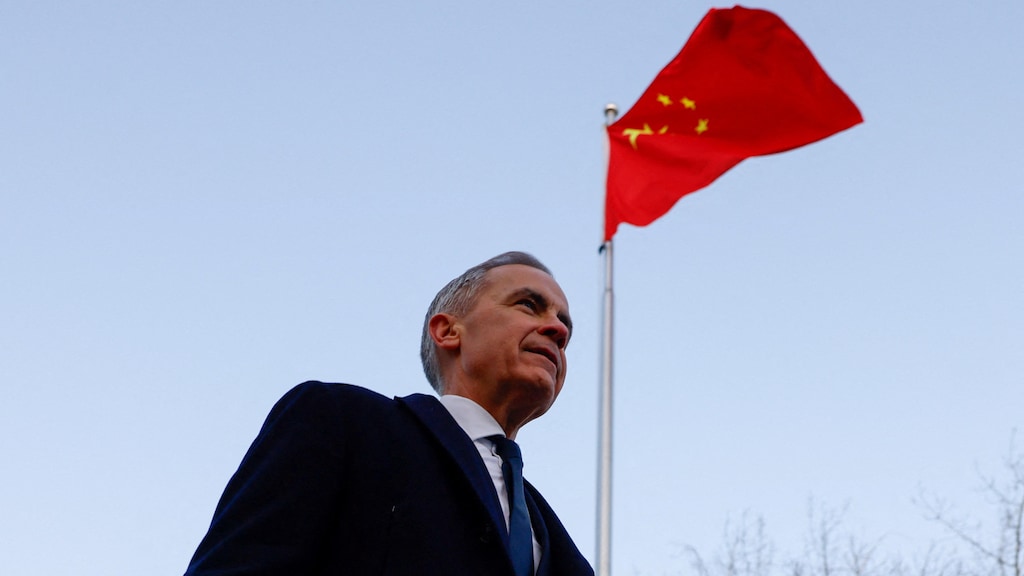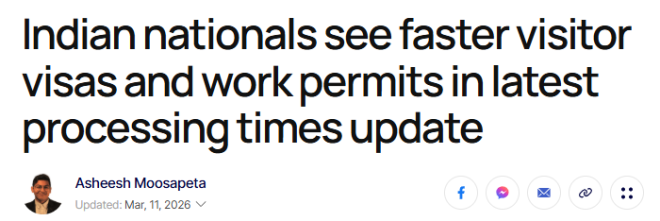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发表了一篇Jane Philpott的评论。她曾担任前联邦卫生部和原住民服务部长,也是前联邦财政委员会主席。她还曾撰写过《人人都健康:一个医生为更健康的加拿大开出的处方》一书。
评论说,在加拿大,我们曾经告诉自己,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保健系统。它曾与冰球一样,成为我们最强大的民族自豪感来源。但是,我们越是认为全民医保是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就越是对现实感到自满,可是加拿大尚未完成建立全面的医保计划。

后来,一场疫情袭来,将我们从自满中唤醒。我们这些在这场传染病中幸存下来的人现在从自满中醒来,意识到尽管加拿大提供了高质量的临床服务,但我们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医疗保健系统。
我们有的只是一个繁杂且缝缝补补的医疗保健系统,在诊所、医院和医疗服务机构里,聪慧而富有同情心的医护人员孜孜不倦、忠于职守,在他们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提供尽可能高标准的医疗服务。
但这不能称之为系统。一个系统必须经过精心设计,将各个部分连接起来,确保它们协同运作,并将其范围内的每个人都包括在内。在加拿大目前的初级医疗保健系统中,缺乏系统规划的问题最为明显。数以百万计的加拿大人正在为寻找家庭医生或初级医疗提供者而苦苦挣扎,因此对全国性协调的需求日益凸显。
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并非一无是处,但还远远不够。医疗保险相当于为医生和医院提供公共资助的全民保险,我们同意集中资源支付医疗必需的护理费用。纳入标准的范围很窄,但没有人会因为无力支付而被拒之门外。在加拿大,我们认为金钱不能成为阻止任何人获得医疗保健的障碍。这一基本价值观必须得到维护,但这还不够。找到足够的钱,并有效的把钱花在医保上,前萨省省长道格拉斯(Tommy Douglas,被誉为加国医保之父)将其称为”医保的第二阶段”。
这就是当前危机的根源。没有一个系统能保证加拿大的每个人都能接受初级医疗服务。在没有战略计划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医生通常根据个人和职业兴趣选择执业地点,而不是根据加拿大医疗保健的总体愿景去最需要的地方去。
对于已拥有家庭医生的人来说,这个医疗系统还不错。与初级医疗服务提供者保持长期关系,意味着无论什么情况,都有人关心你和你的家人:有人与你沟通,理解你,帮助你达到高标准的身心健康。
但是,有这种感觉的加拿大人越来越少,家庭医生也因为无法为每个人提供这样的服务而日益陷入道德困境。几乎没有公共资金支持家庭医生运营所需的物质和行政基础设施,对医生以外的团队成员的公共资助也非常有限。结果就是家庭医生的诊所分布不均匀,没有结构化的方式确保每个加拿大人都能得到持续、全面、协调和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
虽然这种混乱可以通过拨款来弥补,但更悲惨的是患者所经历的痛苦,甚至是过早的死亡。加拿大有近700万成年人没有家庭医生,也无法获得任何其他初级医疗服务。如果你是其中一员,就没有人监测你的糖尿病、高血压或心脏病。没有人支持你戒烟。没有人提醒你是否接受了最新的癌症筛查。当你有紧急健康问题时,你要么自己尝试解决,要么去综合医院的急诊科寻求治疗。
现在建立更好的制度还为时不晚,幸运的是,在我们自己的社区就有一个系统解决方案的模式:早在几十年前,加拿大就决定,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孩子都应该能够上公立中小学。普及公立学校教育的计划已经非常成熟,以至于我们都快忘了这是一个奇迹。学校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而发展。新社区建成后,新学校也随之建成。没有哪个政府会坐等所有社区成员入住后,再筹备建设新学校。
这样的系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初级医疗保健系统: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健康之家”,并保证加拿大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健康之家”的服务。你可能会认为这样做成本会很高,但国际上有证据清楚地表明,建立在初级医疗基础上的系统能提供更好的医疗效果和更低的人均支出。例如,在英国,每个居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在当地的家庭诊所注册,并根据邮政编码选择附近的诊所。与此同时,他们的人均总体医疗支出低于加拿大。这种方法通过及早、主动地干预患者病痛和社会问题,在更长远的道路上节省了开支。
想象一下我们可能的未来:在每个社区,”健康之家”都将是医疗保健系统的前沿阵地,除非你遇到时间紧迫的紧急情况,否则你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健康之家”。在这里,社区医疗团队的成员知道你的名字。他们会用你的名字真诚热情地欢迎你的到来。
试想一下,你的”健康之家”是由医生、护士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团队,根据具体的社区需求提供服务。有些”健康之家”还配有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医生助理、助产士、社工、营养师、药剂师和社区护理人员。在可能的情况下,这个社区医疗团队还包括健康科学专业的学生以及社区志愿者。你不仅能与家庭医生建立长期关系,还能与整个专业团队建立长期关系。
如果你搬迁,新医疗保健系统会根据你的地理位置(一般是居住地)为你分配一个新的”健康之家”。你不需要乞求家庭医生把你加入等候名单,也不需要在这个名单上等待数年。你的医疗服务将就近提供,通常是在你居住地或工作场所30分钟车程的范围内。
大多数”健康之家”可以每周开放7天,每天开放 12 小时。”健康之家”将减轻急诊室的压力,使大医院能够快速、顺利地接受转诊。”健康之家”可以成为居家护理(包括姑息治疗)的协调中心。需要时,该团队的人员可以在家中或社区中为你提供服务,并始终确保上门服务与”健康之家”协调同步,同时实时更新你的记录。你的”健康之家”还可以一站式提供其他健康相关服务,包括公共卫生诊所或营养知识、产前护理或心理健康课程等。其他专科医生定期到当地”健康之家”出诊时,也可以为你提供服务。额外的社会服务,如法律援助、税务问答和出行服务,将使这些”健康之家”成为综合服务体。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梦想。但这个梦想可以成为我们的现实。其他国家已经做到了,我们也可以。在德国、荷兰、新西兰和英国,95%以上的居民都有固定的家庭医生或固定的初级医疗提供者。
要建立这样一个医疗系统,既不能靠手忙脚乱的折腾,也不能靠良好的愿望或政治表态。要建立这样一个医疗系统,不能靠在各省和各地区大派资金,也不能靠虚假宣传,让人们误以为很快就能获得自己的家庭医生。让盈利性诊所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空白也是不可取的。
我们需要政府做出积极的承诺,组织、资助和提供全民初级医疗服务。这一承诺必须有力度。其他发达国家的医疗系统运作效率很高,这些国家通过立法实现了这一目标。挪威就采用了这一策略,并立法规定了人们享受初级医疗服务的权利。挪威人享有比加拿大人更好的医疗保健系统,他们的人均医疗支出也更低。
现在是我们制定《加拿大初级医疗法》的时候了,这一立法可被视为《加拿大卫生法》的姊妹篇。
这样一部立法并不是让联邦政府对省府指手画脚。相反,与其他成功的社会项目一样,《加拿大初级医疗法》将由联邦政府和省府合作制定,并以强大的民主和民意为动力。我们的历史表明,如果在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存在不可否认的公众利益,联邦政府可以在通过向各省提供附带条件的拨款来实现这一点。
像加拿大这样的联邦为各省、地区和原住民自治地提供了极大的自主权。这使得初级医疗服务具有可塑性,从而满足每个地区的需求。然而,联邦政府有义务制定总体规划、协调医疗系统并设定国家标准。为了国家的最大利益,联邦政府可以确立每个人的初级医疗权,并通过胡萝卜加大棒(carrots and sticks)的有效组合来实现这一权利。
立法和实施初级医疗权将需要政治勇气,这种勇气我们只在已故卫生部长贝金(Monique Bégin)的身上见到过。当时是医疗保健领域的一个动荡时期,其特点是医生频繁罢工以及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和额外收费。时任卫生部长的贝京在制定《加拿大卫生法》(Canada Health Act)这部最具标志性、最受珍视的法律时,直面了阻挡公费医疗的各种势力。
2024年4月9日(周一)是议会对《加拿大卫生法》表决通过的40周年纪念日,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得到了议会的一致支持,保证了所有加拿大人都能获得医疗护理的保险。
如今大多数加拿大政治家都不如已故卫生部长贝金一样大胆。我们知道这不可能在一个联邦内阁周期内完成。但是,加拿大某个地方的某个政党将横空出世,将联邦大选资格置于死地而后生,并开始推动制定《加拿大初级医疗法》。
这让人想起了一则古老的寓言故事。故事说的是,一群老鼠生活在对猫的恐惧之中,因为猫可能会来吃掉它们。它们坚信,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猫的脖子上挂一个铃铛,以警告敌人的到来。但是,它们谁都没有勇气实施这个方案,所以整群老鼠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你的团队能给出解决方案固然很好,可是必须有人有勇气实施方案。
通往更好的初级医疗保健系统之路已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建议。它需要的是能够 “敢于冒险”(bell the cat,给猫挂上铃铛)的政治领导。执政不需要纸上谈兵,只需要实际的解决难题。
在《加拿大卫生法》载入史册40年后,我们已经为下一部立法做好了充分准备。该立法将使加拿大从效率低下的各种诊所各自为政转变为一个能够恢复民族自豪感的初级医疗保健系统。也许到那时,我们将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初级医疗保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