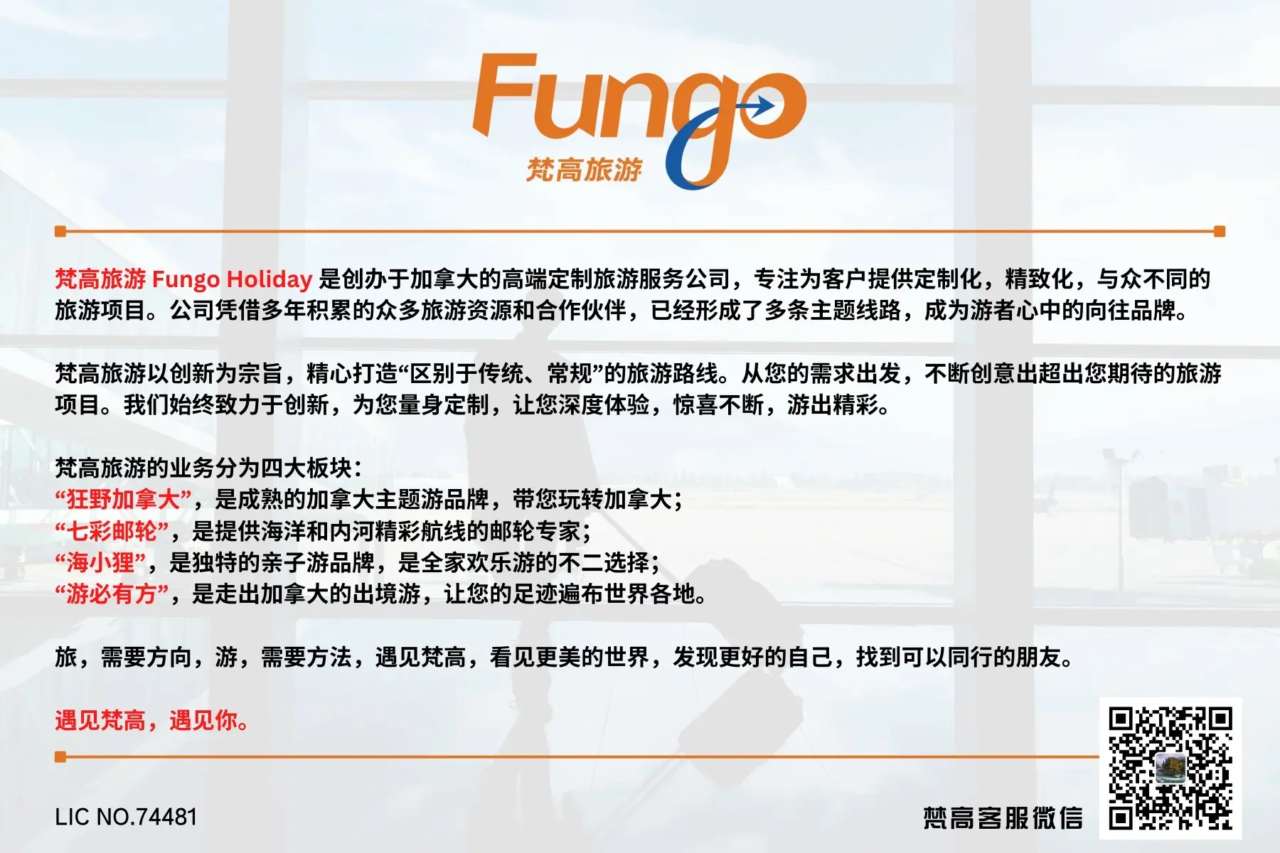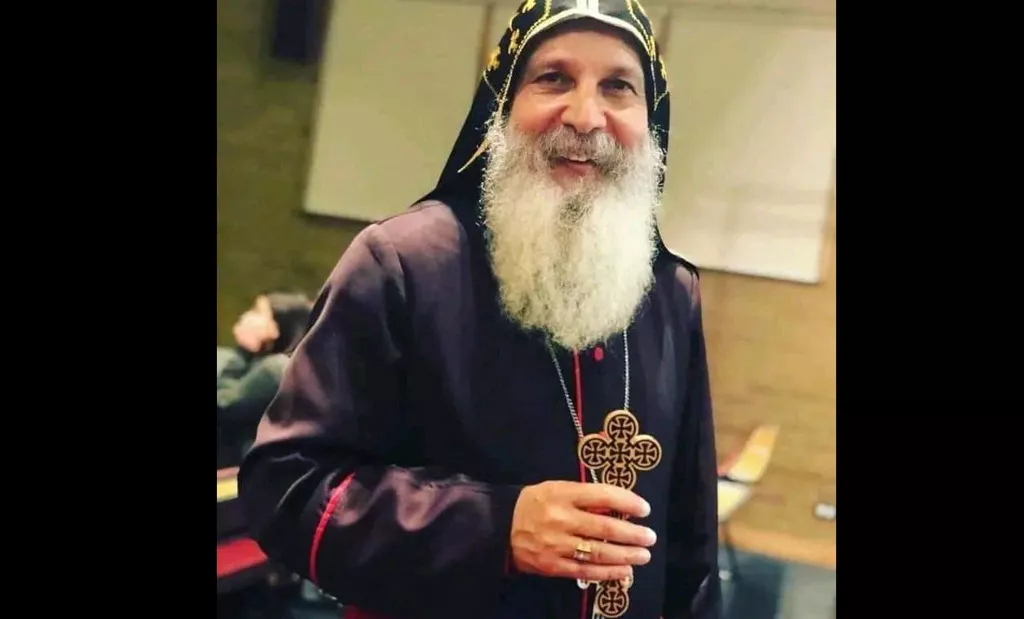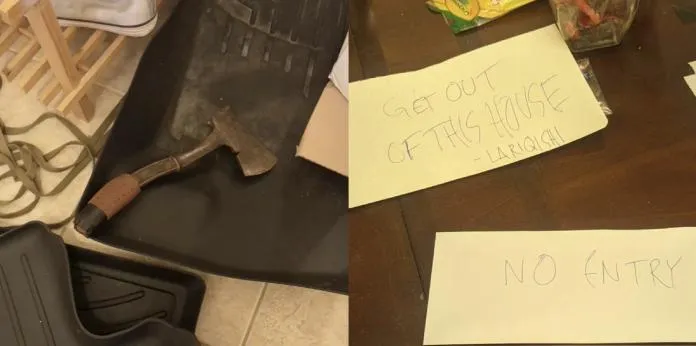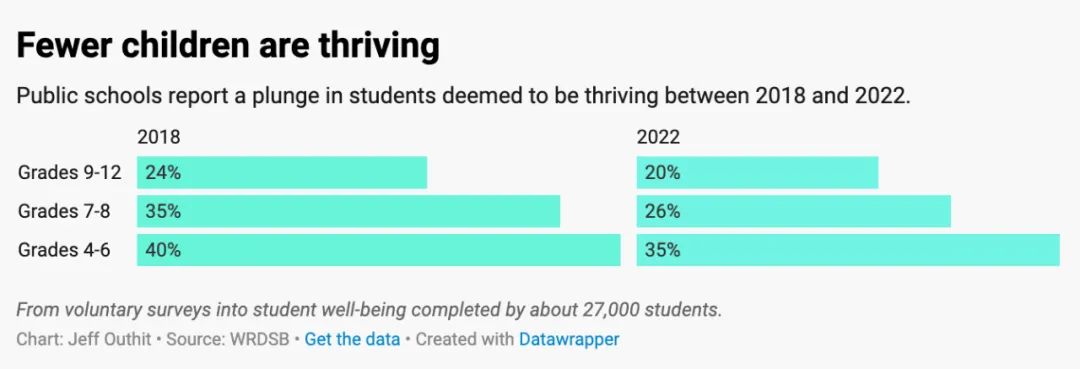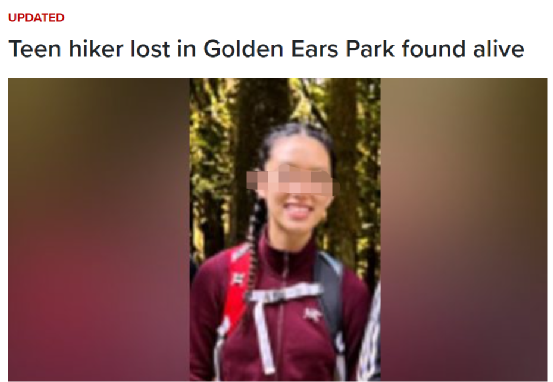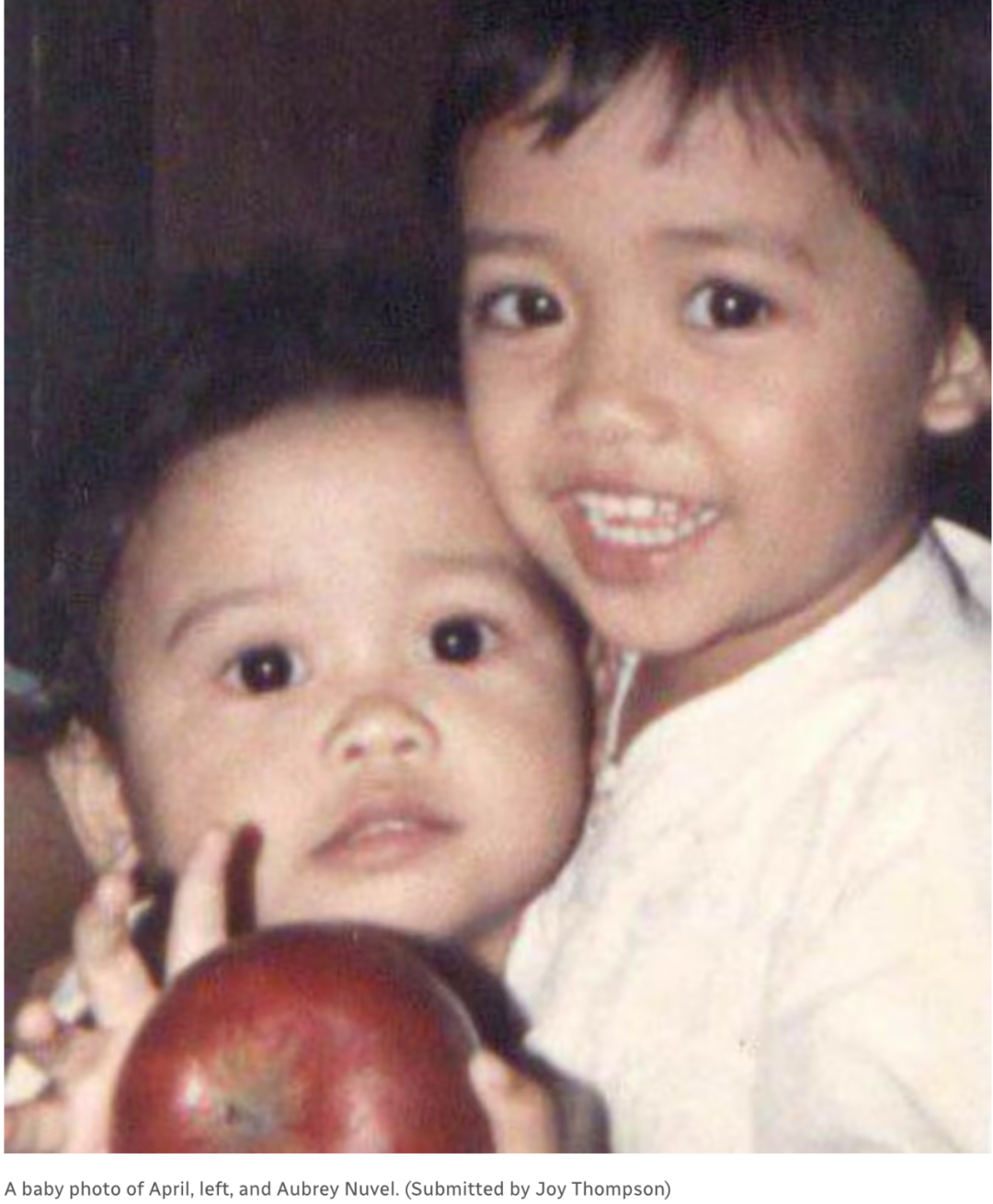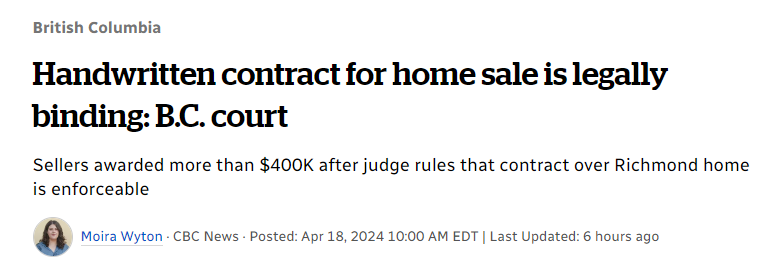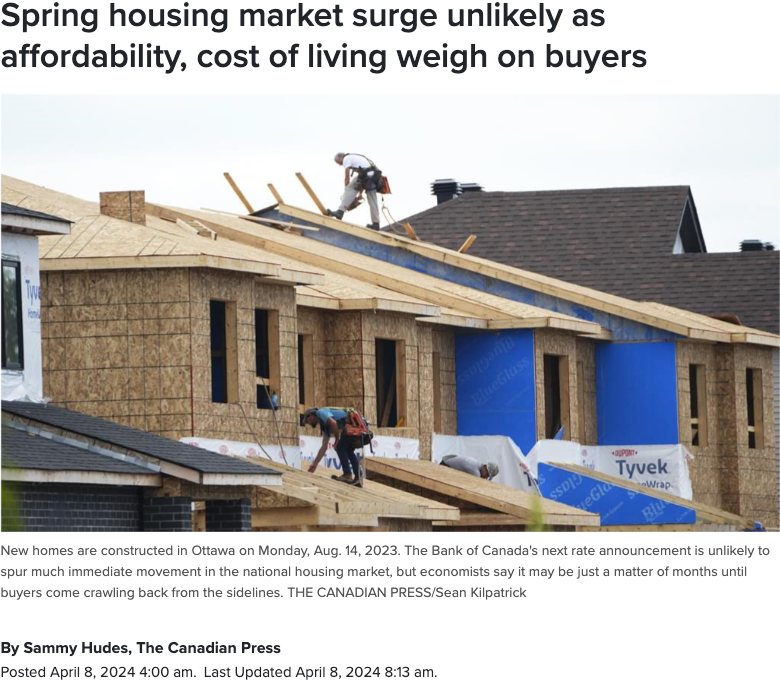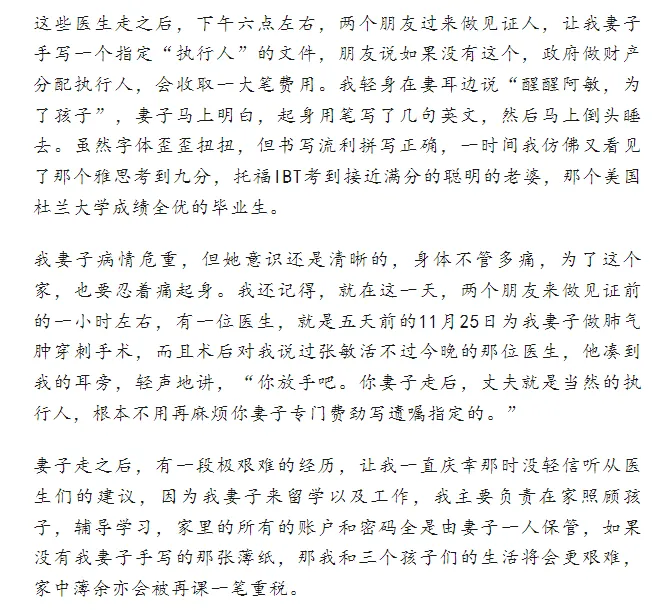幸好,今天上午我媳妇在家翻箱倒柜扒出一只几年前买的掏耳勺,用上它我足不出户就把问题解决了。当一颗花生米大的深褐色耳屎被我撬出来时,那种赫然开朗的感觉真是爽啊!耳痛和耳塞的感觉骤然消弭,既免去了自己耗时费力的麻烦,又节约了纳税人贡献的资源。这些年来像耵聍栓塞一样的小病,我是坚决不去找医生的,因为加拿大的医疗体制让我时时觉得那简直是个慢得出奇的郎中!慢倒也罢了,有时候会让人觉得荒唐。举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吧:
2004年的某天,我那个八岁的儿子不知被谁从背后推了一掌摔倒了,把一颗新换的门牙给磕断了!讲句大实话,那种心痛的程度是我以往几乎没有过的,虽然曾经在医院工作时见过许多各样的伤者。我忍着悲痛说了一句话安慰哭泣着的孩子他妈:「还是感谢上帝吧,伤的不是眼球。」我们送儿子去了北约克总医院的急诊科,当时大约是六点多钟。等了十几分钟后值班护士接待了我们,她看了看带来的那颗断牙,让儿子张了张口,测血压、量体温后就写了张简单的病历,然后安排我们在外大厅轮候区坐等。在焦虑的心情下,我们度过了漫长的两个小时左右。
当听到有人叫儿子名字的时候,我们好像盼来了救星,以为是医院打电话请来了牙医为儿子做紧急处理。结果我们被另一护士引到一个分成很多小间的诊疗区,该区的走廊的长椅上也坐着一长条候诊的人龙,我们仨就再把它延长了一些。又是两小时过去了,悲痛的我们早已失去了该有的飢饿感,甚至连口渴都忘记了,人也开始有点疲惫、虚弱和麻木了。当儿子第二次被叫到名字时,我好像是拖着步子、有气无力地走进不知是几号诊疗间,眼里看到的日光灯好像周围长了白乎乎的毛。在这离奇的第三轮等候中,有位高大的青年男护士例行公事地为儿子做了身体各部位检查,在询问病史的过程中当他得知儿子曾经两次做过疝气手术时,他好奇地问:「你们说有两次手术,可我为什麽只看到一个切口瘢痕?。」我面无表情地告诉他:「没有留下瘢痕的手术是中国一个大城市的儿童医院做的,他们有特殊的缝合方法。有瘢痕的这一刀是贵院两年前开的!」看得出,这位男护士流露出感到意外的神色。
谢天谢地,四十分钟过后,终于有一位中年男医生模样的人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他显得很忙,简短地问了两句,没有再多说一句话,掏出笔来在一张便签上快速地写下了几行英文,递给我们,然后让随后进来的男护士回答我们不清楚的地方。从医生进来到他匆匆离去不到五分钟,我们甚至还未来得及看清他长的是啥模样。男护士把医生的意思转告我们:「今晚没有任何处理,你们带来的断牙也早过了修复期。明天你们就按这位医生推荐的牙医姓名、电话号码联系这家诊所吧。」急火攻心之下,我们问了句让对方莫名其妙的问题:「是免费的吗?」当得知一切费用自理时,我感到这几个小时的傻等简直就是被愚弄了。「花钱的事我还用得着你推荐?!」我当场撕毁了那张五小时等来的便签,并把它扔进了垃圾桶。我很想找医院的上上下下各色人等理论一番,但那天我已没有力气了,而且形成主流的悲痛在心里佔据了大部分位置,以致于没有愤怒之火升起的馀地。况且,这几个小时的损失与儿子断掉新门牙相比还真是个鸡毛蒜皮。总之,那天我们一家人是神情黯然地离开了北约克医院,那是我一生中最有修养的一天。但那也是个假象:因为悲哀抑制了愤怒。
现在,我又回想起一九九九年发生在多伦多一家医院的惨案。一个黑人父亲带着儿子看急诊,因不满医生慢悠悠地工作态度,愤然拔出一把玩具枪把一位医生给挟持了,逼着医生去看他儿子的病。警察赶来后,没有做多少「思想工作」就把这位一时因愤怒失去理智的父亲给枪杀了。那时候,我对这位被警察杀害的父亲并没有太多的同情,不是有句话叫做「上帝让人灭亡,必先让人疯狂」吗?经过我一家在北约克总医院看急诊的这段经历后,我开始越来越惋惜这位黑人的丧命,并认为剥夺他生命的不仅是警察,还有加拿大的低效率的医疗体制,以及他本人的比我更加低下的情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