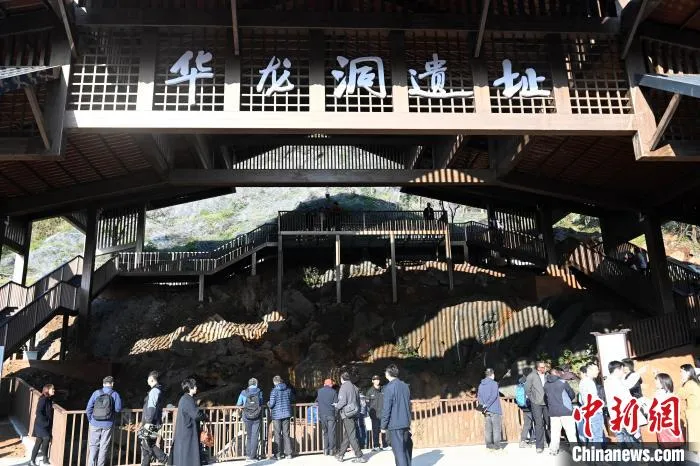我的母亲生于1948年。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母亲,对饥饿有着深入骨髓的记忆,她不识字,倘若知道1600多年前有个孟夫子发出“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的慨叹,定会心有戚戚。母亲亲身体验过那种苦难,让她从小就对粮食视若神灵,奉为圭臬。
我年幼时也尝过饥饿的滋味,虽与母亲经历过的“扒树皮,挖草根”赖以为生的年代有着天壤之别,但也足以让我终生难忘了。那时苏北农村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土地由生产队(就是现在的组)统一耕种,庄稼统一收割,粮食统一保管。人们的生活非常贫苦,生产队统一分配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一年中家家户户都会出现青黄不接的景况。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饥饿这本经几乎适用于所有家庭。
一
我们家7口人,全家吃喝问题由母亲全权掌控。艰难岁月里,母亲精打细算,一粒粮食恨不得掰成几瓣,才让全家安然度过饥荒。
上世纪70年代初,农村主打食材便是玉米、山芋、萝卜,玉米粥、煮山芋是人们“舌尖上的常客”,一天三顿,须臾不离,提起来便会下意识地打嗝,大米白面像是大家闺秀,极少登上农家饭桌。菜也是有的,炒的萝卜丝鲜有油水,锅底不过用油絮子——油絮子是那时农家厨房用品,一般用玉米棒的皮壳制成,玉米皮壳撕成条形,拧成辫体,编成窝状,窝当中填入棉絮——象征性地擦拭几下,就像领导和下级握手,软绵绵没有一点劲道。萝卜丝之于我们,宛若结婚已久的夫妻日日耳鬓厮磨,心中早已腻歪,可又无法割舍,没有它,山芋更加难以下咽。
母亲的精明和节约在熬粥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熬粥是很有讲究的,用饭勺舀玉米面时,踌躇很久,终于舀了小半勺,忽又犹豫,重新将勺子伸进瘪瘪的面袋,倒了点回去。这才放心兑水,她尽量拌出一些面疙瘩,用筷子夹到沸腾的锅里,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面疙瘩在沸水里化为乌有,接着将剩余在勺子底的残面搅成面糊,倒进锅里。
面糊刚入锅时,原本沸腾的水像是一下子没了热情。母亲又在灶膛里加把柴禾,火苗映照着母亲苍白的脸。当锅里的水再一次沸腾,先前的面疙瘩早已修成正果,母亲才放心地用饭勺搅拌,试图让粥均匀,不至于清影照人。母亲的一番努力并未改变现实,粥依然明亮可鉴,光彩照人。
吃饭时,母亲将面疙瘩尽可能均匀地分给年迈的爷爷奶奶,我们兄妹仨和父亲多少也能得到点赏赐。可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刚吃过一会,肚子就开始咕咕乱叫闹革命。我哪里知道,母亲自己从未吃饱过,自己端着清汤寡水,一个人默默躲到僻静的地方喝。
父亲心疼母亲,会趁她不注意,将自己碗里的面疙瘩夹到母亲碗里。这怎能骗得过母亲的眼睛?每次都以父亲失败告终,母亲总能将玉米疙瘩“完璧归赵”。
二
对饥饿有着深深体会的母亲不懂哲学,没听过“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哲理,可她深知穷则思变的朴素道理,她不能只顾管着家中可怜的余粮,将其“分而治之”,那不过是有限的存量,在生产队新的分配计划实施前,终将一天少似一天。于是,她开始谋划增量,考虑怎样增加家中的粮食。一段时间后,母亲终于找到了行之有效的解决途径,那需要她放下卑微而高傲的面子。
捡拾庄稼,在以前,对母亲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她是个极爱面子的人,虽不是大家闺秀,可自小在公社(公社就是现在的乡镇)街道上长大,外祖父灌输给她“事不求人,羞不露面”的传统思想,生活再贫苦,母亲也不会轻易向亲友开口。然而,这一回,母亲决心放下面子,去田里拾庄稼。
经过社员(时下称之为“农民”)们集体夏收秋收后,田里总会有一些“漏网之鱼”。这些残留在田地里的玉米、小麦、稻子之类的庄稼,不是谁想捡就捡的,那得等生产队长一声令下,大喊“放门啦”——放门是我们当地的土话,像是真地打开一扇门,让大家放心进入田里捡拾庄稼——人们才可以捡拾的。
放门的时间大多在凌晨两三点。每当收获季节,母亲晚上根本不敢合眼,生怕错过了放门的大好时机。母亲会坐在床头,借着煤油灯微弱的光线,做些纳鞋底或缝衣服之类的活计,打发时间。有一回,我被母亲“哎呦”一声尖叫惊醒,睁眼一看,原来母亲因为太疲惫,边缝衣服边打盹,缝衣针刺进了手指。父亲劝她躺下歇会,母亲捏着手指,强忍着困意说:“快到稻田放门的时间了。”父亲又说,要不把孩子喊起来,等会一起去拾稻穗。母亲摇摇头说,孩子还小,太困,别喊了。
七岁的那个夏天,我终于可以和母亲一起去捡拾劳动成果了。头顶上星光闪烁,田地边煤油灯摇曳着微弱的光芒,现在想来,那个场景恍如饥饿岁月里闪动的诗意光华。
站在田头,母亲对我说“弯腰就是一个面疙瘩”。多么形象贴切的比方啊!弯下一次腰,捡拾一枚麦穗,积攒一个面疙瘩。放门捡拾庄稼的阵势真是盛况空前,一声“放门啦”,人们争先恐后,恨不得再生出两只手来,有的会为一小撮麦穗的归属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动手。有个作家曾写道,在那饥饿的岁月里,人们为了挣口吃的、填饱肚皮,抛弃了应有的温情。
这似乎带有某种偏见。那年秋天,母亲将舂好的大米,端了半碗给我年迈的表婶。那时家中会隔很长一段时间做次山芋米粥,说是米粥,其实里面的大米历历可数。那半碗米如果熬粥,足以让我们全家吃上好几顿。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一次捡拾稻穗时,表婶和我母亲同时发现了一捋稻穗,母亲凭着年轻手快,抢先到手。可事后,母亲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那半碗大米许是母亲内心深处的自赎吧!
三
不久,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已全面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巨变简直冰火两重天!我能敞开肚皮吃面条了。母亲请我做木匠的二哥打了一张面板,削了一根面杖,专门用来做手擀面。母亲满脸幸福,将面条切得细细的,长长的,那时农村集市上的挂面开始崭露头角,可母亲切的面条丝毫不比它差。母亲会早备好佐料,细碎的葱花,拌上酱,或者淋上酱油,面条出锅装碗后,浇上佐料,小院子里顿时弥漫起幸福的味道。
生活往往这样,已经拥有的东西很难持久珍惜。我十三岁那年,面条成了农家家常便饭,想吃就吃。有一回,我将没吃完的小半碗面条直接倒进了猪食盆,被父亲抓个正着。父亲大发雷霆,抄起大拇指粗的藤条,将我抽得皮开肉绽。母亲保持少有的冷静,根本没劝父亲住手。
那一刻,我的心头泛起一阵冰凉:母亲怎么就不知心疼我呢?深夜里,我从沉睡中醒来,发现母亲并没有睡。她用一条蘸着温水的毛巾,悉心地敷着我的伤口。我的心头一阵发热。
第二天,母亲教育我说,人啊,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本。还说,你才填饱肚子几天,就那么作践粮食,那可是伤害天理的事情啊!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母亲教育我时的神情,她一脸严肃庄重,粮食似乎是她内心深处的神灵和信仰。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浪费过粮食。每当吃面条时,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当年的藤条之苦,隐隐感到一种疼痛伴着温情悄然袭来。
如今,母亲已经年迈。两年前,她不慎摔断了一条腿,做过手术后,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前天回老家,母亲非得做两碗手擀面给我吃。我指着门口说,小卖部不是有面条吗?母亲说,那怎能跟手擀面比呢。我不知道母亲擀面条时,能否回忆起当年的艰辛?但我敢肯定,粮食之痛母亲决不会淡忘。
许是伤腿的缘故,母亲那天擀起面条来很不得劲,做出的面条再没当年的匀称细滑。吃着吃着,我突然泪流满面。
*此篇荣获华联杯母亲节有奖征文活动: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