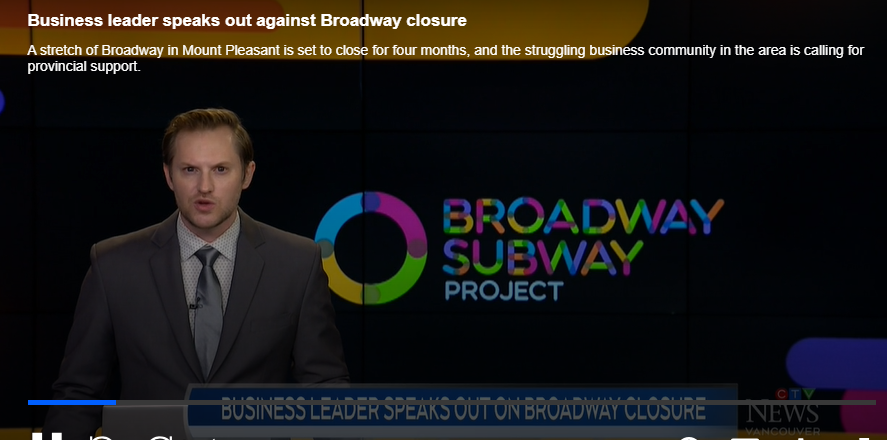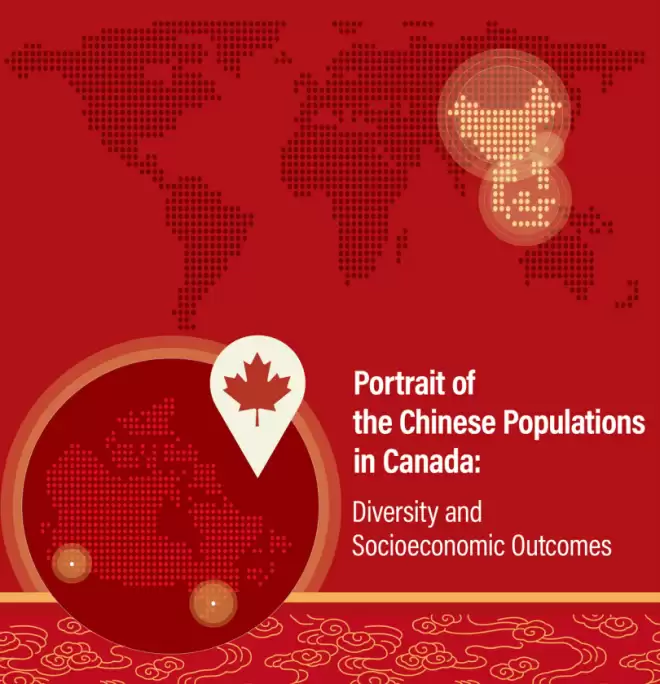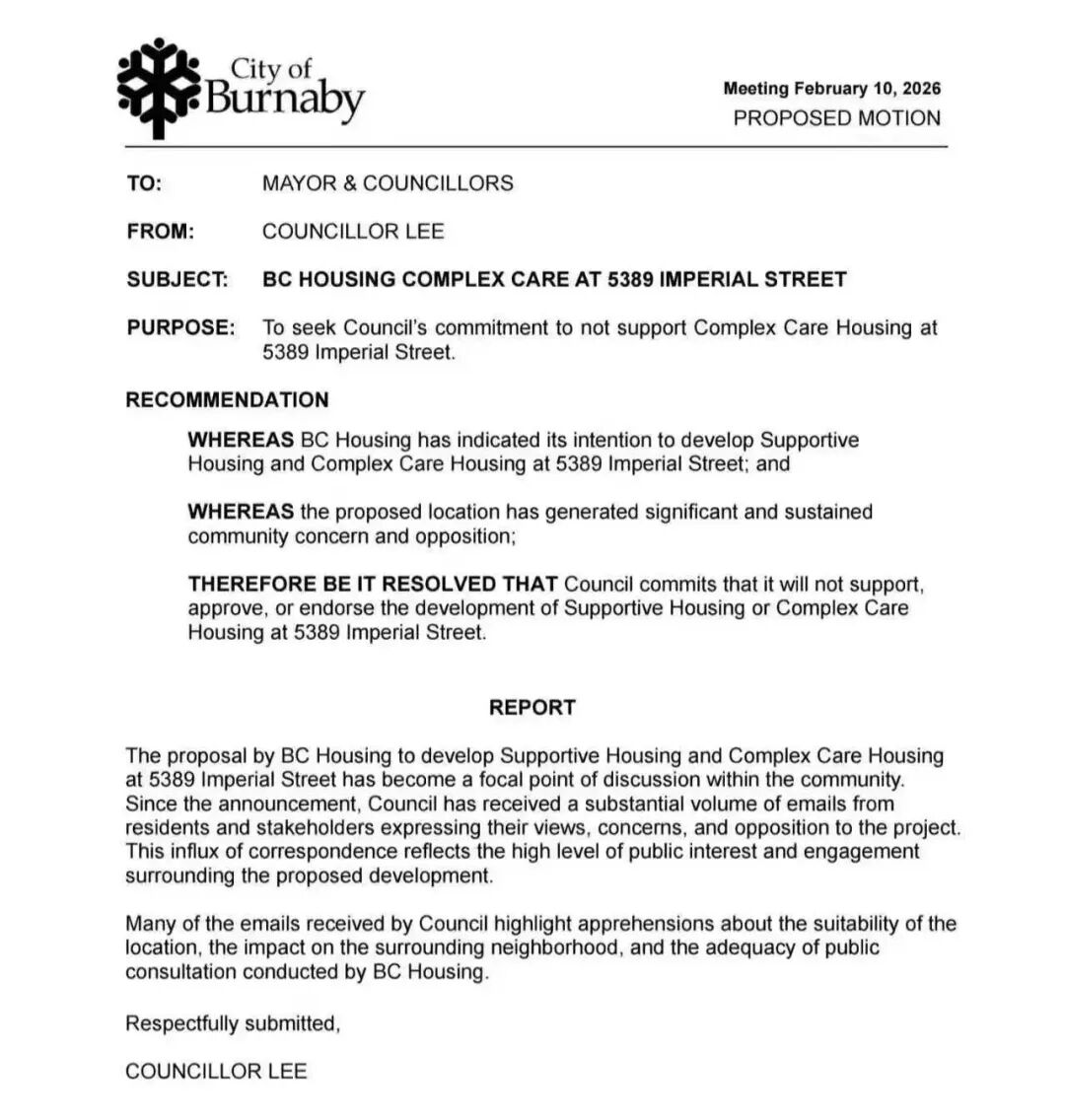2024年,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推出新作《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重塑了信息论、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民主与极权的极端化的产生条件等等,指出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潜在的影响与可能的危机,再一次打破许多惯常的观念与认知藩篱,令人耳目一新。
书中指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简称主体现实)。“在人类开始讲故事之前,现实只有两个层次: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客观现实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比如山川河流。主观现实是个人的感知,比如喜怒哀乐。主体现实“则存在于许多心智形成的联结里”,如法律、神祇、货币等等。“讲得更具体一点,这样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相互讲述的故事中”,就是依赖于人们共同认定才能存在。
人类由于“会讲故事”而产生了更多的联结,让许多人能在一起生活、劳动,创建部落、社会、国家。这一点在尤瓦尔的《人类简史》中详细介绍过。在《智人之上》中,尤瓦尔深入分析了人类会讲故事的“利与弊”——讲故事能促动人类社会进步,但如果乱讲故事则可以通过散布虚假和错误信息而引发纷争、战乱和灾难。
书中详细分析了由于乱讲故事而凭空而出的案例——欧洲的“猎巫行动”。这场历时三百年,导致五六万人被无辜处死的灾难竟然完全是源于“虚假信息”、源于阴谋论。
“中世纪天主教会并没有把女巫看成对人类的重大威胁,有些教会人士甚至还劝阻民众不要猎巫”。到了15世纪20-30年代,阿尔卑斯山附近的教会和学者“从基督教、地方民间传说与古希腊古罗马遗产当众取用各种元素,结合成一套新的巫术理论”,认为女巫的背后“是撒旦领导的一个全球化的女巫组织,形成了一个制度化阴谋反抗基督教的宗教,目的就是彻底摧毁社会秩序和人类”。
但是,在1428-1436年间,阿尔卑斯山地区杀害了200名“巫师”之后,这套理论仍未被欧洲其他地区在意。直到1487年,由于痴迷于“猎巫”而被赶出阿尔卑斯山区的修士克雷默出版的《女巫之锤》成了畅销书后,欧洲的“猎巫”之火才被大面积点燃,并熊熊燃烧了数百年。
《女巫之锤》“迎合了人类最深的恐惧”。制造恐惧、激发愤怒、以仇恨将人们聚合在一起,是从古至今、从石器时代到网络时代最常见、有效、便捷的“团结群体”的方法。人工智能在自助学习后竟然很快掌握了这套思路,因此在许多社交媒体上,无论是算法强推短视频还是机器人编制虚假信息,都是利用人性的这条软肋在增加受众和粘合度。
在女巫阴谋论泛滥后,被处决的“巫师”中甚至有年仅5岁的孩子。“当时,人们只要抓到一星半点儿的证据,不管多么薄弱,就会开始互相指控使用巫术,常常只是为了报复个人受到的侮辱,或是获得经济或政治上的好处。”社会陷入一种癫狂状态,相信女巫的存在、怀疑他人是女巫、并可以随意指控女巫而无需提供任何证据,成了当时的“政治正确”。
“只要开始正式调查,遭指控的人就像是迎来了世界末日”。“被告如果承认自己行巫术,就会遭到处决,财产由原告、刽子手与裁判官瓜分。被告如果拒绝认罪,恰恰证明了他们如恶魔般顽固,于是会遭受各种可怕的酷刑折磨”。“被告早晚会受不了而招供,接下来就是完成处决。”简而言之,一个人一旦受到指控,那真是百口莫辩,死路一条。尤瓦尔在书中列举了一个全家被指控的例子——审讯从10岁的幼子开始,最后全家承认了多项罪行而被处死,“包括以巫术杀死265人,以及造成14场毁灭性的风暴”。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也许会感觉猎巫行动太荒唐,是由于古代人类的认知局限性所致。其实不然。20世纪30年代,“苏联同样发明了一套全球阴谋论,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存在的敌人”——富农。
彼时,“苏联当局一再把经济灾难归咎于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并称富农或资本主义农民为其代表。就像在克雷默的想象中,女巫听从撒旦的命令,召唤冰雹摧毁了农作物;在斯大林主义者的想象中,富农被全球资本主义控制,于是破坏了苏联经济。”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宣布苏维埃国家应该消除富农阶级,并立即鼓励党与秘密警察实现这个宏大目标。”于是,认定了苏联存在着大量被境外势力操控的、破坏本国经济发展的富农,全国上下都要齐心协力发现、消灭富农,成了苏联的“政治正确”。任何人胆敢对这一说法质疑,都是对国家的不忠诚,会受到严格审查,甚至丢掉性命。
“时至1933年,总共约有500万富农被赶出家园,遭到枪决的户主高达3万人。”“只要被打上富农的烙印,就再也无法摆脱。”“就像10岁的‘男巫’,苏联的‘富农’也发现自己被困进了一个存在于主体之间的类别,这个类别被人类的故事所发明,再由无所不在的官僚制度套在他们头上。”
“苏联官僚制度虽然收集了大量关于富农的信息,但那些并非客观真相,只是强加了一些苏联当局虚构的主体间现实。”尤瓦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富农’这个标签完全出于虚构,却成了了解某个苏联人的一个关键要素。”
可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能虚构出一套阴谋论,将某些社会生活中的不足归咎于某个群体使之成为出气筒,或是为了转移矛盾而树立一个假想敌,这就是心理学中所谓的“替罪羊效应”。
除了强权的压迫,大众能自愿接受完全基由想象力所产生的“替罪羊”的存在,是由于:责难、惩罚“替罪羊”能让大众转移责任,避免面对自己的错误或无能;减少焦虑,通过“归咎他人”,降低内心的冲突和挫败感;增强群体凝聚力,共同指责一个“敌人”,让群体内部更团结。因此,在灾难发生、经济下行、社会不稳定时,某些少数族裔、移民、异教徒、异见人士、其他国家等都容易成为替罪羊。
尤瓦尔对“替罪羊效应”的分析极具洞察力——当某些属于不实信息、虚假信息的“主体间现实”通过人类独具的“讲故事”的方法形成阴谋论时,便会形成从主流媒体到官员阶层都将喊打替罪羊视作“政治正确”的可笑又可悲的社会怪状,导致许多无辜的人受害。
不幸的是,这一悲剧不断在人类历史上重现。除了上述的欧洲猎巫、苏联杀富农,还有中世纪由于黑死病爆发对犹太人的清洗;19-20世纪发生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对华裔、日裔的以“抢工作”、“传染病”为由的排斥;二战时德国指责犹太人破坏经济而对其进行的种族灭绝;1950年代美国担心“红祸”而推行的麦卡锡主义;911事件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新冠疫情间的全球许多国家发生的仇亚歧视等等。
而近年来加拿大清理“外国干涉”的社会活动中,也颇有历史悲剧再次上演的势头。
“外国干涉”议题不是新鲜事。最近这一波的起因是2022年魁人党提出BC省列治文市的2021年联邦大选受到了外国(PRC)政府干涉而影响了选举结果,加拿大选举局由此启动调查。调查成了新闻热点,很快便发展为“道听途说”式的爆料。诸如“听说”,“认为”,“推测”这类完全主观的表述赫然成为重磅报道的资讯来源。
到了2022年底,媒体爆料已不局限于列治文选区调查,而是扩展到全加拿大和其他的几次选举,多位华裔背景的民选官员被舆论指责与PRC政府有染。受指责的官员们中,出生地不在PRC、不懂中文较易脱困,另外几位则只能通过打官司来洗清莫须有的罪名。如同几个世纪之前一旦被指控为巫师,“遭指控的人就像是迎来了世界末日”——尽管无需担忧“严刑拷打”,然而被指控者的政治生命基本终结,并受到不明真相的民众的指责、成了千夫所指,还要想尽办法、甚至倾家荡产地凑出昂贵的律师费以求赢得清白。虽然处境不同,但逻辑相似——一旦遭到指控,就几乎无法全身而退。
2023年3月,曾担任过加拿大总督的David Johnston被任命为特别独立监察员,负责审查2019和2021年联邦大选中的外国干涉指控,以及政府应对是否得当。5月,Johnston交出第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大致概括为:“外国干涉确实存在;但没有足够证据表明选举结果受到干涉,也没有发现政府高层蓄意忽视情报;有些引发公众普遍关注的新闻报道有误导性或缺乏证据;政府在制度与沟通上还有很多改进空间;不需要一个完全公开的大型专门调查,但应进行公开的听证与透明度更高的监督。” 6月,由于遭到反对党的强烈反对,认为他与时任总理的特鲁多关系密切而导致独立性不足,Johnston辞职。
同年9月,外国干涉公共调查委员会启动工作由魁省法官Marie-Josée Hogue负责。经过16个月的调查,审阅了成千上万份卷宗、听取百余位证人证词、耗资900多万加币,最终给出七卷本包括51项建议的报告。2025年1月给出的最终报告的结论与Johnston的报告结论很相似,仍然是认为外国干涉存在,却未影响2019和2021年联邦大选结果。对于几位通过打官司来辩诬的民选官员,报告明确指出未发现他们对加拿大的不忠诚及违法证据。他们可能是被外国政府争取影响的对象、也因此引发了加拿大国安局的担忧,但是不应将担忧转化为指控。媒体报道在一定程度误导读者。
纵观事态发展,媒体报道——这个现代社会“讲故事”的广泛传播途径,在整个事件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如同中世纪的猎巫行动,当“故事”被“乱讲”,当不实信息、虚假信息汇聚成阴谋论时,总有人不明不白地被牺牲。如果说时下“乱讲故事”引发的惊涛骇浪尚未彻底淹没被无端指控的受害人,那应该归功于加拿大的现代司法体系已经较中世纪进步千里,给予了被指控者澄清的机会,而不会像猎巫行动中那样被屈打成招。
但是,司法是双刃剑——好的法律能保护社会,不适当的法律则会迫害民众。如何妥善立法需要民选官员们认真考虑。
2023年2月,参议员 Leo Housakos提出Bill S-237。由于该提案针对“敌对国家”的干涉而非全部外国的干涉、关于需要登记的人员和事项不明确,遭到反对后被搁置。

2024年5月,由时任公共安全、民主事务和政府间事务部长 Dominic LeBlanc 提出Bill C-70,即《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反对外国干涉法案)》,6月正式成为法律。这部法律中,有专章(The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简称FITAA)叙述什么样的情形下需要去做登记。然而,FITAA 仍然不够清晰,一些专家和民众担心形成“口袋罪”——由于没有明确限定范围的罪名,给执法留下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容易演变为打压或控制民众的工具。
从猎巫行动到口袋罪,人类社会在通过“乱讲故事”来寻找替罪羊,导致无辜民众、弱势群体遭到迫害,花样翻新,内核不变。历史的警钟一再敲响,愿人类有勇气告别恐惧与偏见,坚持真相与公正,让悲剧成为过去式。